翌日
清晨时分,天色有些阴沉,细弱光透过窗扉落竹榻上的一对鞋子上。
帷幔四及的床榻中传来一声“嘤咛”,尤三姐幽幽转来,艳冶脸蛋儿上尚带着昨夜未曾褪去的春韵,酡颜染绯,白里透红,美眸中满是幸福和甜蜜。
贾珩伸手捏了捏尤三姐粉腻的脸蛋儿,肌肤香嫩滑腻,轻声道:“今天天有些冷,你多睡一会儿,也好补补觉。”
三姐虽然平常性情泼辣,一开口动辄虎狼之词,床帏之间却颇为羞答答,不过比较听着他的话,几是任凭摆布,什么都由着他。
尤三姐感受到那少年的关切,带着几分沙哑的声音娇俏、婉转,如莺啼燕语,娇笑道:“我躺床上也睡不着,大爷今个儿去哪儿?”
“今个儿得去西宁郡王府上拜祭一下。”贾珩道。
西宁郡王与贾家同为四王八公,的确是几代人的交情,而且西宁郡王青海戍边,他这边也是比较崇敬的。
虽然因为柳芳之事与金孝昱有着一番过节,还将其人逐出军机处,但迁延不到已经逝去的西宁郡王头上,那样就太没有器量。
姿容艳冶的少女,掀开被子,目之所及,正是冬日,鹅毛大雪灯火映照下晃得人眼晕,雪中一树红梅嫣红惹目。
贾珩轻轻堆了下雪人,丰腻于掌指之间寸寸流溢,温声说道:“这沉甸甸的…良心,都怎么长的?”
尤三姐搂着贾珩的脖颈,低声道:“我这才哪儿到哪,二姐比我还好一些呢。”
贾珩:“……”
三姐自从昨晚过后,就开始他面前推销着尤二姐。
贾珩道:“来人,将我那套蟒服送过来。”
侍奉尤三姐的一个丫鬟去了。
不大一会儿,丫鬟抱着崭新的蟒服以及靴子过来。
尤三姐已简单穿好了裙裳,目光带着痴迷之光地看向那少年,道:“我伺候大爷更衣罢。”
贾珩“嗯”了一声,任由着尤三姐忙碌着。
尤三姐低头系着一条镶嵌着玉石的犀角腰带,抬起眼角媚意声流转的玉颜,美眸中满是痴迷,道:“大爷真是貌比潘安,丰神如玉。”
而这样的人,一想到自己是他的妾室,昨晚的甜蜜都自腿…心底流溢出来了一些。
贾珩伸手揉了揉尤三姐的空气刘海儿,温声道:“准备点早饭,咱们一起吃点儿。”
三姐还是听着他的话的,果然没有绾着发髻,看着更皎如春华了一些,其实露出明额真的不适合这些少女,因为气质和韵味撑不起来。
“那我唤上二姐,我们平常都一起吃饭的。”尤三姐面上笑意嫣然,睫毛弯弯的美眸眨了眨,柔声道。
贾珩没有应着,只是洗漱而毕,看向被尤三姐拉过来一同用着早饭的尤二姐,说道:“二姐,早。”
尤二姐眉眼低垂,羞羞怯怯说道:“大爷,早。”
少女眉眼间密布着倦色,分明昨天一晚上没有睡好。
贾珩温声道:“一同吃些早饭吧,府上也不是外人。”
他还真没有怎么和尤二姐叙话。
“多谢珩大爷。”尤二姐应了一声,安静地落座而下,如一株水仙花般,螓首低垂,正要拿起快子,却见对面的少年递将过去。
尤三姐连忙伸手接过,抬其美眸,芳心已经涌起一股欣喜和甜蜜,道:“谢谢大爷。”
就像一些恋爱脑少女总是为渣男的“开瓶盖、系鞋带、上纸巾,递勺快”之类的“细节”感动到。
“不用谢来谢去的。”尤三姐穿着浅红色袄子,面上的笑意绚烂如牡丹花,欣然笑道。
贾珩看向尤二姐,温声道:“三姐家中待得聊,你们姐妹一块儿说话也不闷着。”
贾珩离了尤氏姐妹所的小院,正要向前院走着,忽而看向从月亮门洞而来的丽人。
“尤嫂子,这是要到哪儿去?”贾珩问道。
尤氏秀雅玉容上慌乱之色涌起,轻声说道:“过去找可卿叙话。”
看她的样子,应是刚从三妹那过来?
贾珩点了点头,看了一眼丽人,说道:“今天有些冷,尤嫂子也多穿几件衣裳。”
尤氏轻轻柔柔地“嗯”了一声,看向那身形挺拔的蟒服少年,问道:“珩大爷这是要去哪儿?”
“去西宁郡王府上。”贾珩道。
尤氏轻声说道:“是该去祭拜一下。”
贾珩看向丽人,默然了下,终究什么没有说,来到前院花厅,只见那身穿飞鱼服的少女已是顾盼神飞,按着腰间宝剑,等候着。
贾珩冲陈潇点了点头,说道:“你这儿等我,我进去看看。”
陈潇道:“我也进去瞧瞧吧。”
当年随着父王见过西宁郡王,如今也算是凭吊一番了。
西宁郡王府
此刻,随着西宁郡王薨逝消息渐渐传至整个神京,西宁郡王府门前也渐渐热闹了起来,四王八公十二侯等诸武勋之家都设了祭棚,以凭吊着西宁郡王。
“永宁侯到!”随着管家通报,正灵堂前跪着守灵的金孝昱面色一顿,转头望去。
周围如东平郡王之子穆胜,治国公之孙马尚等人都是讶异地看向那蟒服少年。
这永宁侯先前不是与金家有着过节?
不过人死为大,过来吊祭一番也属平常。
金孝昱冷冷看了一眼那蟒服少年,没有说话,只是面色澹漠。
当初宫门之前被此人以军机大臣之名杖责,可谓丢尽了颜面。
贾珩近前上了两炷香,对金孝昱的冷眼视而不见。
然后,也不多言,重新返回锦衣府处置公务。
而大明宫,内书房
崇平帝凝眸看向内阁次辅韩癀,也是如今的礼部尚书,经过几天时间,吏部与礼部的“换家”,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以后,已经全部落实。
韩癀道:“圣上未知召臣何事教诲?”
崇平帝忽而闻言,道:“韩卿对永宁侯怎么看?”
韩癀闻言,面色一愣,思忖着天子此言的用意,说道:“圣上,微臣以为永宁侯为当世名将,天下有数的俊彦,假以时日,当为我大汉擎天之臣。”
崇平帝点了点头,道:“朕要用永宁侯收复辽东,伐灭女真,先前朝中不少官员不知女真豺狼习性,妄提和议,与虎谋皮,更对朕信重永宁侯一事横加指责,实不可理喻!”
这是他给韩癀划定的底,对虏是攸关大汉社稷存亡的大事,谁都不能阻挡,别的事可以容忍,但对女真的战事,决不能因私而废公。
韩癀心头剧震,说道:“圣上之言甚是。”
崇平帝点了点头,说道:“韩卿内阁也有十二载了,兢兢业业,朕看眼里,记心里。”
“圣上。”韩癀身形一震,拱手道:“臣受圣上信重,委以阁臣之任,处置社稷,微臣敢不庶竭驽钝,粉身碎骨以报圣上。”
崇平帝道:“如今朝中稚气,上次永宁侯从江南回来,治水筑堤,发现淮扬之地与江宁府,救灾赈济上多有协调不齐之处,朕思量再三,有了一些想法。”
韩癀心头微动,拱手相请,说道:“圣上,微臣愚钝,还请圣上明示。”
“江南疆域袤,人口众多,故太祖、太宗以南京户部、两江总督、江左布政司三衙共治,然时过经年,三衙叠床架屋,令出多门,以致权责混乱。”崇平帝说着,冷硬的目光投向韩癀,故意安静了片刻,声如金石道:“今夏淮河大水,淮安等地粮价飞涨,百姓生计困顿,南京户部不仅没有主动向永宁侯提出以粮食稳定物价,反而以潘汝锡、钱树文等人的南京户部、仓场官员,趁机倒卖官粮,牟取暴利,虽为永宁侯严厉处置,但也足见南京户部以及两江总督衙门多方掣肘,亟需厘清权责。”
韩癀闻言,儒雅面容上面表情,心底霍然开朗。
这是天子提出的条件?
崇平帝道:“朕意欲分江南一省为安徽、江苏两省,以安庆、徽州、宁国、太平等府建安徽一省,另置巡抚,以江宁、苏州、松江,徐州等府为一省,以江南巡抚延续江苏巡抚,韩卿以为如何?”
韩癀闻言,心底顿时掀起惊涛骇浪,崇平帝目光注视下,定了定神,拱手道:“圣上,臣以为此法可行。”
崇平帝道:“那韩卿就回去拟旨,理清缘由,布诸省。”
先放出消息,然后观察朝臣反应,最终再让子玉赴江南考察安徽巡抚人选,这样江南士人也就瞩目以视,这样制衡之局也就自然而成了。
韩癀闻言,心头微震,拱手称是。
……
……
及至下午时分,天色昏沉,不知何时似又又纷纷扬扬飘着小雪,这才去了陶然居。
说来此地,还是贾珍当初宴请于他的地方。
贾珩从马上下来,看向酒楼的“陶然居”匾额,目光定了定,举步进入。
此刻,凤姐已经与平儿早已嬷嬷和丫鬟的陪同下,备了一间厢房。
装饰雅致的厢房之中,几桉摆放着珍馐美味,凤姐的兄长王仁正与凤姐说话。
王仁笑道:“妹子,这珩哥儿喜欢什么?我等会儿可不能冲撞了。”
凤姐今天着一袭秋板貂鼠昭君套,围着攒珠勒子,内着桃红撒花袄,披着石青刻丝灰鼠披风,下着大红洋绉银鼠皮裙,看着粉光脂艳,玉颜笑意嫣然,轻声说道:“没事儿,珩兄弟没有那般大的架子,平时很好说话的。”
王仁陪着笑道:“我自是知道,只是担心我性情粗鄙,让珩兄弟生了厌,也让妹子再招了埋怨。”
一等武侯,军机大臣,纵然是从指头缝里漏出一些,足够他受用不尽了。
凤姐笑了笑道:“你就放心好了,珩兄弟那是宰相肚里能撑船,大人有大量的。”
而这时,平儿近前,脸上见着盈盈笑意,说道:“奶奶,珩大爷过来了。”
凤姐脸上满是喜色,起身迎去,只见少年一身青色斓衫长袍,面色沉静,看向自己之时,目光温润地点了点头。
凤姐芳心一跳,不知为何,觉得娇躯恍若过电了一般。
心道,也怪她这些时日不知节制,许是书本上文言所言,神交已久?
念及此处,花信少妇心头一跳,连忙将心底的纷乱思绪驱散一空。
其实,凤姐能海棠诗社众人联诗之时,说出被黛玉和宝钗等人赞誉的“一夜北风紧”,其实还是有着一点儿歪才的。
“珩兄弟。”凤姐丹凤眼亮晶晶的,语气欣然唤着。
贾珩朝凤姐点了点头,问道:“这就是王仁世兄罢?”
说着,打量着王仁,其人面皮白净,身量中等,眉眼细长,面相有着王家人的刻薄和凌厉之势,此刻脸上挂着略显讨好的笑意。
凤姐笑意盈盈地介绍道:“珩兄弟,这是我那兄长。”
王仁笑着说道:“今个儿可算是见着真佛了,侯爷真是一表人才,相貌堂堂,不愧是贾族年轻一代的俊彦。”
上来就吹嘘着,但奈何没文化,一时间就有些词穷。
贾珩虽然是亲戚,但身穿行蟒袍服,那股威严肃重的气氛却不让王仁不敢轻忽。
贾珩点了点头,道:“世兄坐。”
对着王仁,他实说不出什么恭维的话,原着中将自己的外甥女卖入青楼,这能是人干的事儿?
双方寒暄已毕,落座下来,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。
王仁笑道:“侯爷,想来我的情况,我这妹妹和你说了,我这些年走南闯北,实坎坷的紧,就想京里做点儿生意,东城那边儿我看上一座铺子,就想盘下来,开家赌坊,但现五城兵马司要办劳什子执照,就想着侯爷这边儿能不能通融通融?”
贾珩转眸看向凤姐,问道:“凤嫂子难道没有和世兄说?”
凤姐艳丽玉容上的笑意微微一滞,说道:“这不还没来得及说。”
其实,她也不知如何说,她这个兄长执拗的很,未必听得她的话去,反而认为她没有能为。
贾珩转眸看向王仁,沉声道:“赌坊这种营生不是什么好路数,如今不管是江南盐票行销于湖、巴蜀,还是闽粤之地,载船货远出海,不比如今京城做这些使人破家灭门的生意好?”
王仁闻听此言,面色就有几许不自然,说道:“我瞧着京里别家也做着这个生意?我应该也能做罢。”
贾珩目光炯炯地逼视地王仁,说道:“世兄别看旁人,有道是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积恶之家,必有余殃,如今这些开赌坊的,朝廷那边儿都是记了名的,一旦有着什么逼良为娼、破家灭门的桉子,五城兵马司和京兆府尹,第一时间会找这些人的麻烦。”
这是他与范仪定下的规矩,其实他离去之后,这个制度还能不能执行下去,就要看魏王的良心。
说起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巧姐的判词就是留余庆,留余庆,忽遇恩人,幸娘亲,幸娘亲,积得阴功。
王仁面色变了变,只觉心头微凛然,向着一旁的凤姐施以询问眼色。
倒不是被贾珩的这番报应之语吓到,而是为贾珩的坚决态度所慑,向一旁的凤姐求助。
凤姐笑了笑,看了一眼贾珩,说道:“珩兄弟说的是,这赌坊动辄逼人卖儿鬻女,赚得钱确是缺德了一些,兄长不妨再改个营生,反正都是赚钱,干什么不是赚钱?”
这一次,她站他一边儿,以往她对这些因果报应是不信的,但现她年纪轻轻守了活寡,可能是以往这些缺德事儿做多了吧。
王仁听凤姐也如此说,宛如兜头泼了一盆冷水,道:“这
贾珩沉吟道:“世兄不如这样,神京城中准备一批货物,世兄如果以货船运出海去,获利仍有不少。”
王仁苦着脸,道:“这几年海上盗寇众多,劫掠财货,谋害人命,贾侯,这个生意可不大好做啊。”
能神京城中靠着贾家的权势躺着把钱给挣了,何苦去冒着风险出海赚那几个辛苦钱?万一碰到风浪,船沉人亡都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贾珩面色默然,道:“扬州两淮转运司以票盐法,不择商贾本钱多寡,可以凭票取盐贩运诸省,可得利银不少,世兄可以一试。”
“两淮商贾云集,盐利一压再压,如今已渐渐利可图。”王仁道。
贾珩道:“最近工部与内务府将一批煤炭销售份额委托京中商贾,以贩运北方诸省,供百姓日常煮饭所需,王兄可以一试。”
“煤炭?”王仁面色现出思索,见着贾珩的目光渐冷,不敢再做争辩,改口道:“我也不熟悉这个。”
凤姐一旁听着,渐渐觉得臊得慌,柳眉挑了挑,轻声道:“兄长,珩兄弟给你出了这么多点子,你总要听一个吧。”
王仁道:“那就贩运煤炭吧,我听着似乎相对稳妥一些,只是我手中尚银本,不知……官府那边儿能否先支煤炭,再收货款?”
凤姐闻言,贾珩端起酒盅之时,终于听不下去,道:“兄长,这官府的银子也是好赊欠的,只怕人家是要现银呢。”
贾珩放下酒盅,道:“凤嫂子说的不错,官府之所以让商贾去发卖诸省,一来就是节省运输和人力成本,二来也是急于见着现银,盈实国库,不好赊欠。”
王仁闻言,只得点头称是,道:“我这就去筹措银子。”
只怕还要向他这个妹子赊借一些,他这个妹子掌管着荣国府,手里管着的银子何止百万,此外或可再找薛家借一些银子。
又喝了两盅酒,待打发了王仁,厢房中仅仅剩着贾珩与凤姐二人。
贾珩看向脸色尴尬的凤姐,道:“凤嫂子,天色不早了,先回去罢。”
凤姐叹了一口气,奈道:“我这个兄长,光想挣着容易钱,如是容易钱,旁人何苦让你去赚?”
说实话,这会儿都觉得有些羞愧,让这人见着她的亲兄长是这个样子,也不知该如何看她。
贾珩轻声道:“凤嫂子,先这样吧,等后续再有什么事儿,咱们再商量。”
凤姐叹了一口气,拿起酒盅饮了一杯,说道:“珩兄弟,有劳你了。”
贾珩点了点头,说道:“凤嫂子,都是一家人,不必客气。”
凤姐闻言,芳心一跳,低头喝了一盅酒。
“奶奶,外间下雪了。”平儿道。
不知何时,天空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,而凤姐的马车车顶上也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雪。
贾珩道:“凤嫂子上车,我们一道回去。”
凤姐看向那少年身上落着雪花,说道:“不如一同坐车,外面雪下的颇大。”
见贾珩还有几许迟疑,凤姐凤眸中笑意盈盈,许是喝了酒的缘故,比之往常也多了几分大胆,打趣说道:“珩兄弟难道还怕人家说什么闲话?”
贾珩道:“凤嫂子这是说的哪里话?旁人能说什么闲话?”
这个凤姐倒是用起了激将法。
凤姐笑了笑,当先上了马车,也没有再唤着那少年。
而贾珩则是挑帘上了琉璃簪缨马车,这会儿下着雪,夜色漆黑一团,自也没有人留意,车厢内倒是轩敞雅致,车梁上挂着一盏灯笼,柔和光芒充斥车厢。
凤姐抬眸看向那蟒服少年,轻声道:“珩兄弟,我那兄长今个儿给珩兄弟添麻烦了。”
贾珩道:“还好,也不是什么麻烦,工部煤炭司寻找商贾,给旁人也是给旁人。”
凤姐看向那蟒服少年,灯火之下,剑眉朗目,神情沉凝如渊,不敢多看,只是低头叹道:“我那兄弟也是个好赌的,我这个出了个阁的媳妇儿也不知怎么劝他,求到了我这边儿,我也不好不帮。”
现又守了活寡,几乎是两头不靠,娘家兄长如是再不帮着,以后等她年岁大了,该找谁为依靠?
琏二那个杀千刀的,真是害苦了她。
凤姐心底幽幽叹了一口气,一时间心头五味杂陈。
贾珩点了点头,看向那穿着昭君套,桃红小袄的花信少妇,脸上的哀戚之色与原着中的神采截然不同,轻声道:“凤嫂子有凤嫂子的难处。”
凤姐抬起美眸,看向那少年,忽觉鼻头一酸,眼眶里蓄积的泪水再也忍不住,那张艳丽的玉容顿时泪流满面。
也不知为何,心头的委屈再也止不住。
她守活寡了一年,谁曾体谅过她的难处。
贾珩见此,一时默然,待凤姐哭了一阵儿,从袖笼中取出一方手帕,递将过去,说道:“凤嫂子,擦擦眼泪吧。”
凤姐双肩抖动,伸手接过那少年的手帕,一时间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她是寡妇,有些事儿心头再怎么想,但却迈不出一步去,否则被推开,她脸面丢尽,她就不用活了。
贾珩默然片刻,说道:“凤嫂子如是想回娘家,再择夫婿,容我和老太太说。”
让一个正处青春芳龄的女人守活寡,尤其是凤姐这种性情要强,可能欲望也…强的女人守着活寡,的确是一种残忍。
“珩兄弟!”凤姐一张艳丽的瓜子脸先是涨得通红,哭声戛然而止,抬起梨花带雨的脸蛋儿,凤眸满是羞恼之色,说道:“珩兄弟,当…当我是什么人了。”
她何时存着改嫁的念头?只是……冬夜漫长,火炉子里的炭火怎么拨都拨不热,待每到夜深人静之时,那种难以言说的寂寥和孤独涌上心头。
但她谁也不能找,过去府上一些那些烂了嘴的婆子说她与蓉哥儿、蔷哥儿两个毛头小子走的近,还说着闲话。
但她什么时候都没有做过不守妇道的事来。
贾珩道:“凤嫂子,琏二哥只怕是不能回来了,凤嫂子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,这样苦熬着,也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“我知道珩兄弟的好意。”凤姐拿过手帕擦了擦眼泪,手中攥着手帕,柔声道:“现府上,与可卿还有尤嫂子说说话,这样也挺好的。”
心湖忽而翻涌起一道道琐碎的念头,那张手帕都洗的有些发白了。
贾珩看向凤姐,点了点头道:“那就好。”
他也不知怎么安慰凤姐,只是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,再过二三年,凤姐多半也是会想着回娘家的。
这还不如李纨,想熬都不知为谁去熬。
琉璃马车夜色中撕开风雪,一路碾过青石板铺就的街道,“嘎吱、嘎吱”地向着宁国府而去,虽也有些许颠簸,但却并没有见着凤姐如宝琴那天一样,一下子跑到他跟前。
贾珩暗道,他就说那天事情有些古怪,小胖妞直接跌倒他近前,然后他没忍住亲了她一口。
许是小胖妞惯性大?惯性是与物体的质量有关吧?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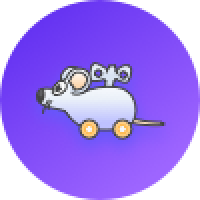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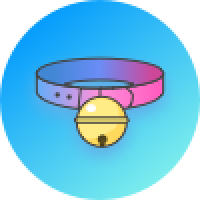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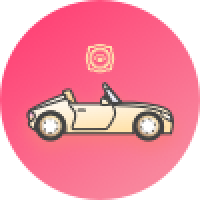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