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请我进去坐坐?如何都是老相识,即使客套未必能令你我时常把酒言欢,但偶尔也要做做样子才好。”
铁匠铺老汉再回头时,灯笼低下已然站着个神情玩味的中年男子,青须青发,气度飘然自如,浑然没有擅自来访的迹象,而像是导入你远游归来,难得卸去浑身疲惫劳形,也不管精瘦老汉如何答复,自行走到铁匠铺里,瞥过一眼不久前云仲坐的空地,再没言语。
除云仲之外,这间分明立在闹市当中的铁匠铺,就再无熟人来访,却没想到这位自行登门,当即令老汉皱起眉头,不过到底还是没应声,自行前去里屋拽出柄太师椅,使两截锈铁垫住太师椅一腿,却还是显得晃悠,但与云仲那等近似于凭交情闲扯的姿态,老汉此时收敛大半,举动反而很是拘谨。
铁匠铺里摆设当然好不到哪去,既不是容易惹富贵的行当,且终日飞火四溅,屋中摆设大多都要蒙上层灰白转黑的厚重尘灰,很是衣衫不整油灰满头的老汉站到屋中,如何看来都是比面皮俊朗衣衫纤尘不染的青须男子更是合宜。
“大驾光临有失远迎,不知有甚指教?闹市地界的铁匠铺寸土寸金,难不成是打算收回到自己手上,再将我这无家可归的老朽赶到外头自己乞食?”
“这等事,几位可不是没做过,未必是老朽偏要给几位扣帽子。”
不需东檐君多言语什么,自然能
从老汉口中听出近乎是不加掩饰的怨怒,故而索性就不再挑好听的言语,撩衣袍下摆端坐到那张立地不稳的太师椅上去,竟也是身形不动不摇,稳稳坐到太师椅上,端详四周,最后失声笑起,“还是那等模样,明明在此界中本事不亚于我等,怎么还是老德行,不通转变,过后定要吃亏,不如尽释前嫌,把臂同游,也好过日复一日在此无所事事的好。”
今日东檐君来访,老汉自知多半是要耽搁一阵,于是又将炉添上火,蹲到旁边咧嘴直笑。
习惯老者怪诞举动的东檐君也没多问,端坐半晌过后,自行走入铁匠铺后院里头,俯身看向后院里头那一方古井,伸手将古井搅浑,如顽童一般守在井边,搅动过好几回,瞧着力道并不大,但很快井口正中清水就翻腾起来,当即涌出数朵水花,水花当中,捧出条足有两臂长短碗口粗细的鱼儿,但不知为何停到井口前,狠狠望向东檐君。
鱼儿背上驮有十几枚眼目,模样极是瘆人,大小错落,分列鳍边的时节开合不定,但大多皆是怨毒,鳞片抖动之间,眼目也跟着开合,相当骇人,如今口吐人言。
“我当是哪位债主上门,却不想如此多年过去,还是你们四人,看来这搬救兵的举动,到头也未曾成行,仅剩下你四个老不死仍在此地躲藏身形,真叫人心头舒坦。”
“你又不是人。”东檐君呵呵笑
起,半点也不急,反倒窥见这尾鱼从井中窜出的时候,笑意更甚,直起身来笑道,“我等几人在此地待得倒是习惯,纵使出不去,腾挪地方也不算小,可身在一井死水里头,就有些五十步笑百步,哪里来的傲气。”
“有事就说,无事滚蛋。”
“近来这片小界有些许缺漏,虽是补齐大概,但还是略有不足,特来求片老鳞修补此界,这才不惜夜班更深时候,前来叨扰。”
很难想出分明只是尾游鱼,此刻竟然能由打鱼儿面皮上瞧出神情来,怨毒得意,尖细声笑道,“好一个修补此界,老夫等了不下千百年,好歹等到此界有损,好让那位顺蛛丝马迹前来,将尔等一一诛灭,今番又来求老夫自损,用以避祸,世上哪里来的好事,都让你几人占全,恨不得将你等剔骨抽筋,如今却是正巧如愿,不借。”
对此东檐君仍报以一笑,双手扶住井口,“拿来。”
井口中清水骤然跌落一截。
那尾身背眼目的鱼并不理会,正打算翻身回到井底的时节,井口动摇,井水又低矮一截,眼见得无多少流水。
这尾鱼身负眼目,大有来头,也正是如此原本不过一头得道行的大妖,能将亘古长存此界牢牢占住,若非是多年后来了这四人,多半真能凭此界再进一步,十几枚眼目分应世间七情六欲,贪悔痴愚,当年同四君交手时,生生撑住三日,才被四君所擒,
镇压此地多年,虽再无多少进境,可也终究并非是东檐君一己之力所能压制,但眼下这等场面,却是令游鱼很是惊愕,连忙掉回头来,重新跃上井口,死死瞪着东檐君。
后者还是重复那两字,拿来。
井中水枯。
“你乃是天地开后,少有的大妖,当年也理应觐见过那位,被它知晓你这一界被我等占住跟脚休养生息,凭它的性情,足下难道以为自己也可逃出生天?不论人间还是修行界内,大多贪生,我几人将你困在此间,既不伤性命,亦未曾有甚出格举动,只令这片天下能替后世修行之人讨取些好处,如若坐等此界分崩离析,惹出蛰伏多年的那位,你我下场,并没有多大分别。是死是活,我想你虽是大妖,行无拘束,善恶不明,但总有贪生念头,不妨细想,这绳头两端不止拴着我四人,还有你这位被迫让巢的喽啰,如何能置身事外。”
平平淡淡一番话,却是使得游鱼身后十几枚眼目皆尽微合,许久也没接茬,更未曾再有挣扎举动。
等青须的东檐君手持枚月盘似的鳞片,要迈步离去的时候,重新变满的井中,游鱼还是不禁开口戏谑道来。
你们四方君也不过是天下的一片微末缩影罢了,全然够不到神仙二字,也皆有贪心痴念,何来的傲然,大概想当年灵智未开的时节,作恶未必就有老夫少,甚至出于生来便是力强者,作恶没准
比我还要多些,如今却又要摆出圣人模样来教训旁人,真是不知羞。
“差距就在于此,都是由懵懂年月,知晓世事,再到如今老谋深算,可我几人知善向善,知晓罪过,必尽心弥补,所以与你不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。”
等东檐君回到铁匠铺的时候,老汉已将那块好铁烧得通红,可到头也没动锤,锁双眉蹲地很是烦闷,见东檐君迈四方步走回,手头多了枚鱼鳞,当下就晓得此番多半如愿,故而也是没好气熄了炉火,就要逐客关门,却不料眼前人还有话说。
“被压了许多年,这回总归是翻身做主,还要多添点心思看守好后院这头鱼,毕竟根基不浅,我几人又是忙碌命,实在分不出多少心思时常前来,全仰仗您多出力。”
“巴掌还没挨,甜枣就管够,各位还真是讲究人,”老汉咧开满嘴牙无声笑笑,“老朽不堪大用,借四位的手翻身,说到底不过是从头上游着条鱼,变成坐镇四位尊人,也没什么差别,同样都是挥手而来翻手而去,像那鸟雀与五座山岳,同前些日子抹白脸唱戏的恶蛟,不就是随心取用?”
东檐君沉下双眉,“南阳君恐那小子能耐不济,走的偏门路数,理应受些指责,可那后生,不是已经将剑还给你了?所以往后他要上山,孤身应付那些位山间人的时节,只能靠自己的剑术,但连一柄趁手剑都没有的剑客,真还
能叫做剑客?”
话里话外的意味,再直白不过。
这双剑固然是从你老人家地盘中取的,可既行的皆是好事,且替此地镇压那尾背眼目的妖鱼,怎么都不为过,云仲纵使是听你劝,掰了那子规五岳两柄剑,还山还鸟,致使无趁手兵刃,无论是心善至此还是喝高被三言两语蛊惑了心智念头,结果摆在眼前,怎么都是欠人情。
没再浪费口舌,临行之际,老汉突然问东檐君,这块铁他敲打了许多年,却怎么也没想好要打成什么物件,人情欠下就不嫌多,愿听闻指条明路。
一向脾气淡然闲云野鹤的东檐君则不愿再多说,只道想要什么物件就打成什么物件,无需同别人询问。
但出门离去时,还是没忍住说了句万兵皆下品,唯有剑气高。
顺理成章的,独守铁匠铺的老汉将未冷下来的好铁,敲了几千锤,但还是没捶出个细胎,与其说是剑胎,倒不如说是捶出一柄三尺余的铁尺,不曾开锋未曾淬火,就这么缓缓晾凉过后,捧将起来前后端详,而后像是随手甩水似,甩出铁匠铺外,瞬息踪影全无。
天外多出道凌厉光华。
那柄铁尺先上高天,再下城楼,风声大作,最后稳稳当当悬在云仲府邸前,却再不肯朝前去。
因为府邸外头几步,云仲趴到镇宅石狮背上,就这么打起鼾来。
铁尺悬在剑客的头顶。
几只鸟雀纷纷前来,好奇看向这位动作无拘束
的剑客。
朦胧月色一袖洒落,照在云仲后脑上,也落在很远处连绵山岳上。
这片天地无变幻,却好像冥冥之中给这位醉酒的剑客大开门户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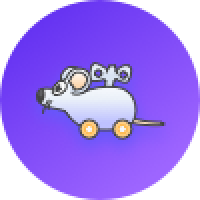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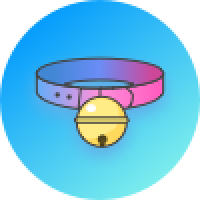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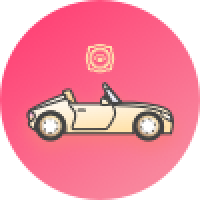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