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东境大元山中的修行人,都晓得胥孟府乃是依傍环山而立,既能见燕祁晔其人胸怀,亦能知晓这么处依山而立,而因当年流寇盘踞,显得风水不那么好的胥孟府,当真靠得并非是强敛那些玄之又玄的风水气运,方才有眼下这般浩大的声势,硬是自修行人山门,近乎杀穿整个大元,使得东西贯通。
不过更少有人知晓,从大元战事起就很是神出鬼没的燕祁晔,实则最常去的地方,就是胥孟府环山最高处,进一步可触及天穹,而退一步则万劫不复,崖壁处光洁可见,纵然夏时潮雨时节,不生绿苔,莫说老猿愁攀,长蛇难行,而灿灿星斗过此峰时,亦需避让。
这是燕祁晔在山巅孤身盘坐的第十日,纵是胥孟府到如今尚有人主持大局,不过算计下时日,这位老府主孤身一人踏上环山之巅,实在是有相当长久的时日,不过事先燕祁晔就曾嘱咐过,断不可令人登峰半步,即使是向来依仗老府主威势,在外很是有几分跋扈的少府主,照旧是不得近山巅一步,违者必斩。
其实已然有许多人嗅出端倪,只是既不便说,同样也不好断言,想来胥孟府收拾大元诸座仙家宗门,那已是数载前的旧事,早在胥孟府还未曾意欲一手掌握整座大元时,就已是将这等后患尽数解去,现如今哪怕是这位境界精深而不见底的老府主碍于五绝面皮,将各修行山门前的牌匾归还,这些个修行宗门,依然是被燕祁晔牢牢握在手上。既是断然不会为早已失势,唯胥孟府马首是瞻的修行宗门扰动心念,更是早就将各方事宜托与那等精熟一道的亲信,更有那位历来很是叫人心安的病书生统辖兵马,虽不久前吃了回甚大的亏,但远未够到山穷水尽地步。
凡事有不解处,实则安下游离未定心思,安安稳稳趁饮茶闲暇时琢磨一番。大概有七成之上乍看之下顿感糊涂的事,即可生出些自个儿的念头通途,不见得真,可还总有些道理。
能够扰动寻常人心的,往往是今年年关时节,抛去鸡毛蒜皮所耗的银钱外,可否尚留有些余财。稍稍宽裕些的人家,大抵总要寻思片刻儿郎年岁已足,是否要有个一技之长,学文学武,或是手艺营生,总是要关乎往后吃喝二字,而最是不起眼的零碎银钱经层层盘剥苛取过后,可否尚能留有应对一时之急的冗余,跌打磕碰,风寒旧疾,总是择选那等最是不该来的时节,不由分说闯入一家门户,架势同那些位杀人不眨眼取财又伤命的马贼流寇相比,好不到哪去。更是有老者需供养照看,有幼儿啼哭乞衣食,边驮山便踏完卵,最是举步维艰小心翼翼,乃是大多天下人所担忧操劳,时常愁苦困心所在。
而转至燕祁晔身上,能动摇搅扰其心思,以至不甚平稳的,怕是唯有如今这座近乎为两方打得崩灭,十面狼烟万事俱休的大元战事,才最能惹这等修行道内,心念城府极坚实的高手忧扰不定。
很多人乃至于胥孟府里身居高位之人,都时常要默默抬头,朝环山山巅处望去,此处飞雪最盛最密,遮天蔽日,近乎使山巅同阴沉沉天穹锁到一处去,见雪浪似云雾升,见云雾似飞雪停,但从来没人能看个通透,山巅处到底有甚变动,或是山间那位老府主,究竟有何算计担忧。
往往高处不胜寒,行至高处,方才得见寒天其中愁云几许,浊雪几许。
可山间的燕祁晔或许未必要这般想。
老头自打领着那位自个儿相当看重的门房小童一并上山巅过后,近乎无一刻闲暇,先是赏雪两日,专挑那等飘摇时最是摇曳生姿浮动轻盈的无根雪,结结实实盛满三五枚木桶,而后很是显摆地掏出六七盏不过两三指宽窄的紫泥小茶盏,使无根雪煎茶,轻饮慢品,顺带观雪势浩大,评头论足一番,落在小童眼中,却总有些装腔作势之嫌。好在是燕祁晔虽可辟谷,仍未忘却替小童携来些肉食,穿于枯枝处,在一方狭小茅屋内凭火盆烤得油亮,下场便是险些灼伤胡须,很是有两分灰头土脸。
至于这位胥孟府之主,究竟所思所想为何,小童看不出,旁人同样看不出,只觉得是在闲暇玩闹。
后头足有七八日,燕祁晔只是教小童一趟走拳功,虽说是老头自个儿打得虎虎生风,可小童练过足足两三日,半点妙处也未看着,只觉得这拳法同胥孟府里最是不入流的门道手段相比,还要相差一大截,奈何架不住已是认了师父,只得是愁眉苦脸练起,时常倒要替燕祁晔添茶送水劈柴挑火,相当不情愿。自打从拜入燕祁晔门下,认了个便宜师父,燕祁晔便从小童心里的神仙爷,变为府主,而后又变为便宜师父,到如今已是成了个相当不靠谱的贪吃贪喝老头,足见小童受过多大的委屈。
可始作俑者却毫无半点悔改之意,闭目安神,饮茶观雪,却又处处看不惯小童练拳,说是绵软无力,找只垂死野松鸡前来,怕是力道都要更高两分,忒惹人看不上眼。
估计山下胥孟府内之人,同样也想不到,这位老府主上山一旬,一事未做,只是坐于藤椅处,听了十日大雪扑簌。
而直到今日将晚时,有一架车辇由几人抬起,晃晃悠悠冒风雪沿路上山巅,方才有了些不同。
“堂堂胥孟府府主,不去惦记战事,反在此自顾欢愉,八成许多人猜测,都是落空。”
车辇内里有位听来言语声很是醇厚的中年人朗声开口,听口气竟还有两分笑意,并不存留有什么存心取笑或是甚幸灾乐祸意味,甚至早在这车辇上山前,就牢牢锁死这车辇内男子气机的燕祁晔,都不曾觉察到半点异样或是违心。
“我倒以为被自家山门栽培的逆徒废了你双足双臂,能令你张凌渡自弃自怨,却不想反而使你心念又厚实一重,当说不说,到眼下如今我还未见过你这等古怪的人,闲暇无事时不思进取,而偏偏是待到所珍之物遭人悉数扯个干净,忽然之间顿悟,好一把敲不碎的贱骨头。”
远未有多客气,燕祁晔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,也就更没有上前相请的意思,自行将小盅内茶汤嘬饮酒殆尽,自行观望纷飞素雪,令远山心甘情愿披得重重白袖。
车辇内的张凌渡也不恼,只是伸出枯枝一般的左手,将衣衫扯起,方便御寒,但走下车帐,对于一位双腿齐根断去,经络尽死的人而言,并不是什么容易事,于是才要起身,就是无奈笑笑,索性就这么坐于车帐之内,同相当看不起自己的燕祁晔慢条斯理闲话二三。
“至于晏几道,我倒没什么埋怨的,人总是要替自己奔忙些,倘若连自己都谈不上什么忠实,又何谈什么忠于师门,况且我这当师父的,算不上教过他什么不得了的东西,反而是他自行学来的,要更有用些。”此时一身清瘦,险些受晏几道折磨致死,浑身旧疤林立的张凌渡,言辞之间却是不带有什么凡间气,顿了顿才继续道,“我猜这人一定是不在人世,府主以为,我所说可对?”
别人不知,可燕祁晔却知晓,张凌渡此行所为何事,不然也断然不会在这等明令禁止上山的时节,乘夜色而来,更是不会说出方才这番话。
张凌渡要的便是求死,所以近乎是不加犹豫,就将这番揣度燕祁晔心思的话说出口,而恰巧揣测得的确不差。
晏几道这等人,自有其高明之处,否则也断然不会在那等大元宗门尽皆受难的时节,借风而起,顺势夺来大紫銮宫宫主之位,倒当真是替胥孟府做过不少事,可惜有些人能借风势自起,却始终因过重的心机野心,坐不稳来之不易的位置,死在燕祁晔手中,就当然不是怪事。
“下山去吧,你对我无用,或许在黄覆巢那有些用,不过那书生从来不嫌浑身沾染多少污名,老夫我还要点脸,别遭天下人指着老夫鼻头骂街。”
张凌渡神色一黯,也未再说些什么,辇车退去。
头上白发白雪掺杂到一起的老人抬头,眼下既无月色,也无落日,仅剩余将夜色都险些映明的雪光,从渌州壁垒边关一路沿袭至此地从未被战事侵袭的大元东境,近半掌大小雪片极其稳固,任由山间凛冽冷凉罡风自低处吹向高处,自高处又盘旋直下,砸落开无数朵银白色,遭夜色嵌黑的尘埃浊浪。
当然还有个孩童在打那套半点高明都谈不上的的拳招。
燕祁晔起身摸摸那孩童头顶,小童只是觉得头顶来了一阵不轻不重的风,随后又突兀地重归寂静,因此很狐疑地看了眼老头,没由来就觉得这老头是不是站得又高了些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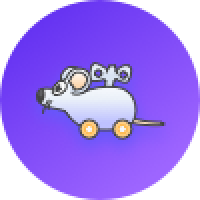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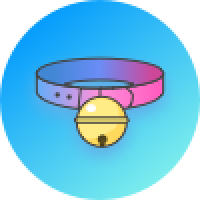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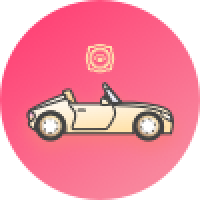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