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荀元拓出门相迎时,才发觉看似很是有些鬼精明的张亚昌,实则还挺仁义,这四碗豆花没多要,除张亚昌窦文焕这两位形影不离冤家和师兄弟之外,许久未见的周先生破天荒将发妻一并接来,统共四人分乘两座车帐,当然就将这笔不小的开销,压到家境极好的窦文焕肩上,这其中当然是少不了张亚昌推波助澜,相较于只同荀元拓讨要四碗豆花,对这位大师兄如何都算是下手极轻。
至于这位师娘,荀元拓早年间自然是见过,如今再度上前行大礼请安,却发觉这位先生发妻与几载前,容貌并无甚分别,养护得极好,甚至现如今的周先生,单瞧面皮,大多人都要觉得同自家夫人差个一旬的年岁。
不过瞧见自家先生脸上始终挂着笑意,荀公子也是释然笑笑,就将几人请入铺面其中。
久居齐梁学宫,张亚昌窦文焕二人入皇城纳安,当然是有些雀跃,尤其是这位奇丑无比的张亚昌,浑然不在意自个儿面皮吓人,活泛得紧,窦文焕则是仍旧抱有富贵书香门第公子的矜持,但只需瞧其吞吃豆花时的模样,就晓得齐梁学宫里头的吃喝,怕是分外单调,连强装城府过人,掩饰住欢愉的贵公子,此时却是端起盛豆花的瓷碗,吃相相当不讲究。
“先生此来,不妨就在徒儿府内小住,平日里空空荡荡,住处甚多,恰好再同先生论论棋道,许久不
曾试手,都快忘却了这一道上的本事。”
周先生比起自家这三位徒弟,吃相最差,连事先说好在外留些面子的夫人,都是有些看不过眼去,见周可法将豆花吃到胡须上,不动声色回手摁到周先生腰间,只消拽起些许边角皮肉提起些,而后使两指一扭,晃上两晃,就足够使常人疼得五内颤抖,止不住讨饶,只是当着三位徒儿的面,周可法只得是吃力挤出一丝笑意,收拾好胡须,唤荀公子出门一叙。
“二品官,与一座同正一品规模相差无几的府邸,为师都有些艳羡,短短几年入二品官,说不上是古来未有,历数大齐到现如今,也不会超过五指之数,我家徒儿,果真是出息了。”
不知是嫌豆花铺面人多口杂,欲换个僻静地方说话,还是当真有些担忧,时隔多年再返皇城,会不会替自家徒儿招引来什么不应当有的目光,周先生刻意避过大多过路人,只找寻条荒废幽深的小巷,随意挑选了处石阶,垫上布帕坐下,也递给荀元拓一枚,还不忘叮嘱两句,“这可是你师娘出门前挑灯缝的,布料上好,仔细着些用,前两日为师这身新衣裳蹭了些油渍,险些叫你师娘掐下两块肉去。”
荀公子接着过那枚周先生口中,挑灯缝制的上号布帕,上头针脚杂乱,间隔时宽时窄,有点惨不忍睹的端倪,再瞧瞧自家师父这身新蓝布棉袍,针脚同样是怪
异杂乱,半晌都没吱声。
八成连周先生这一手针线活,与出门在外自行动手解决衣食的本领,都是被这般逼出来的。
“住处一事,自是有去处可住,现如今你小子可是二品官阶的上齐重臣,做事自然不得如此欠考量,莫要忘却上回你师父从上齐离去,是出于何故,好容易这些年月随荀文曲那老混球,洗得差不多干干净净,再沾染上,可是要添无数麻烦。”
周先生坐定石阶处单腿翘起,神情悠然,显然是此番进京,心境又有不同,虽是身在檐下,抬头向上看那一线天时候,总是要稍稍眯起眼来。
就这么一处区区小巷。师徒之间将近几载以来种种事,皆是一桩桩一件件讲来,周可法身在齐梁学宫当中,谈不上两耳不闻窗外事,可消息自然是不比如今的荀公子灵通,单就大元一地内乱事,经由暗子与荀文曲剖析过后,荀公子自然是心知肚明,将此事说来同自家先生听时,也是难免夹杂些自身见地,反而要比身在皇城其中更为坦率。
成王败寇暂且按下不表,如只论那位少赫罕种种举措,着实是位雄主,不过在荀公子看来,论用兵道奇正相生,方才可称将才帅才,而这位少赫罕所行种种,步步皆是涉险,如只知晓一味用奇,便可说是此人做事擅决断,尤喜一蹴而就,凭一招棋定胜负,走投无路时,乃是挽天倾扶大厦的雄主,但如
若治国仍只擅奇,而不擅平和,大元未必就要比现如今的境况强出许多。
内忧外患之下,必要显现出强横一面,而倘如是内乱尽解,最为妥当的举措,实则是藏锋。
木秀于林风必摧之,何况西有紫昊始终觊觎,更素有争端,再者因洙桑道一事结下梁子,占去其商贾一道最为眼热的银钱往来,南有东诸岛隔海相望,弹丸之地,夙兴夜寐成日巴望着占据夏松大元这等平原地,隐忍藏锋数十年,大抵总是有朝一日欲掀祸事,倘如是一味不知收敛,未必就没有战事比肩继踵而来。
上齐则与大元全然不同,虽说文强无武弱,积弊已久,经大元风满楼搅动,不得不将扶武抑文一事推到风口浪尖处,起码眼下圣人意志,已是将其点明,可但凡有操之过急,或是猛药服下,必定要使得上齐动摇,如欲稳妥,未必大刀阔斧,或许更应当软硬兼施,文火炖煮,才最是贴合上齐境况。
“话讲得没错,不过为师还是要点明两句,”周先生从始至终都相当安静,听自家徒儿讲来,直到荀公子收尾时,才微微点头赞许,“照你所言,实则大元这位新主,算计得并无过多错漏,他强我弱时节,需事事缓和下来,明知不能胜却偏要硬接,不智之举,可要当我压过敌手时节,便竭力要快些,毕竟不只单单有早日收复全境,整顿黎民安抚苍生的考量,更是为
快一步将这等祸端铲除,好尽快赶在山雨前,替自己夯厚一份家业。立于不败。”
“上齐文强武弱,根深蒂固,倘如是动得太快,朝堂动摇,国本动摇,必不是什么好苗头,疾症在骨里,倘如是直白添一剂猛药,没准病人登时气绝身亡,可若是一味讲究温补,此消彼长,药力不足清理病患处,那此事就推行不得,何况但凡是有些见地之人,已然能够窥见到往后烽烟遍地,固然要放缓些,但快慢一事,本来不就是由你等把持?”
“高明庖厨擅控文火,医道圣手,知晓药力分寸,譬如一叶扁舟从十万山行至纳安,你要做的既不是撑浆点桩,使这扁舟离岸,也不是确保这扁舟靠岸,而是持桨划船,舟行快慢缓急,是顺流而下,或是逆流缓进,其中避让礁石暗流,火候才是关键。”
一席话恰好点在荀元拓最为狐疑处,可偏偏这次,周可法并没有多说,而是在最为至关紧要的点上,稍稍戳了一指。
“时隔多年过后,再掉过头来,你小子就会觉得眼前这事,实在是再容易不过。”
天色尚好,深冬时晚照斜阳,最容易惹人生出怜惜,狭窄巷子其中两户人家,飞檐隐生辉光,五色釉瓦衔头继尾,在冬阳播撒不遗余力里,缠镀上一重烫金底色,如此这般一遮,天地略无踪,更莫要说近在咫尺的皇城内院,不过仅能见这么一线天外,层层叠
叠,由暗色转为烫金般不那么炙热的冬时天穹。恰似笔墨勾描,泾渭分明,而又在极短暂的时节随流云变换,继破晓过后,再度归复到寻常天色,三点两抹奇异的明暗色泽,留为余韵。
“这片天地下,做事最容易的,需向上看,谁人在高处,谁人有时就可说了算,即使是世人往往加以所谓法度,所谓道义种种牵制,但若是跳出圈外,不曾立在局内,就要晓得冷眼旁观时,看得更为明朗清楚,上位之人下定心思做这件事,当然不会有多难,尤其此地是继大齐国运的一方皇城,圣人握持的权柄,远比大元等诸地更为牢固。若是连这等白得的功业都抓不住,回头出去可别说是我徒儿,忒丢人,让为师这张老脸往哪搁。”
“之所以你觉得此事棘手,并非是畏惧此事本身,而是对于身在高位应当如何自处害愁,也难怪有此念头,寻常人都是先步入府上,再踏足内院,而你却是先登内院,而后再去往府中,由奢入简,先做了圣人器重青睐的来客,而后再步入朝堂,当然起初手足无措。”
正如周可法所言,青柴其中的荀公子,虽往日不见得贫寒,然而有这般泼天富贵压来,一时同样招架不得,只觉心头沉重,难免就有瞻前顾后,畏首畏尾的心思,如今被自家师父戳破,相当尴尬咳嗽两声,最后还是嘿嘿一笑。
“那哪能瞒得过师父法眼
,师父到底是师父,哪怕日后徒儿官居一品,还是比不得师父学富五车俊逸超群。”
“不错不错,有长进,那为师可就接下这一记马屁了。”
许久不曾见过的师徒二人相视大笑,眼中皆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侥幸,直至在豆花铺面里头的师娘久等两人不归,在巷子口外高声喊了声周可法,穿着身相当别扭衣衫的先生,才相当狼狈地连忙起身,缩头快步,携荀公子走出巷子,讪讪赔笑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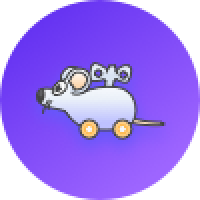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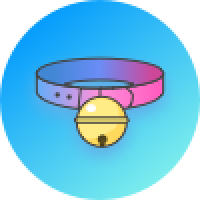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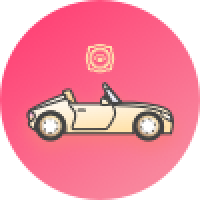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