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白衣说完,又似总结道:“此便是白衣扰敌、御敌、攻敌三策也,元让将军,这攻敌虽为下策,但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,一举拿下沧水关......只是需军中擅江湖功法之人领军,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......不知元让将军,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么?”
说着,他以目示夏元让,更朝着苏凌的方向努了努嘴。
夏元让如何不知,也算正中下怀,他看了看苏凌,语气尽量放得平缓道:“这攀援绝壁的功夫我思来想去,军中诸将皆不如苏长史......不知苏凌,你可否有兴趣啊?”
苏凌一翻眼睛,一口回绝道:“不去,不感兴趣......”
他这句话噎得夏元让直翻眼睛,若非有事相求,夏元让早就动怒了,如今只得耐着性子道:“这事若成了,可是大功一件,不知你为何......”
“不为何......怕冷!”苏凌未等他说完,便截过话道。
说着,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抱着肩膀斜睨着夏元让。
郭白衣见状,只得苦笑摇头,打圆场道:“既然如此......那便不为难苏凌了......反正这攻敌之策也是下策,元让将军不妨考虑考虑中策和上策吧!”
“嗯——!”夏元让呼了口闷气,这才又道:“也罢......夏某以为,中策和上策并用,营中加强防守,谨防敌军偷营,我军更要派
出小股人马,轮番袭扰沧水关......”
众将闻言,也频频点头。
郭白衣见此,遂神情一肃,朗声道:“既如此,便如此决定了,各位将军即刻便速回本部,先查清本部死伤人数,理清本部人员......以免细作混入其中,然后各部配合,轮流日夜值守,以防敌军偷袭,同时编出袭扰沧水关的小队,轮换袭扰沧水关,让蒋邺璩那厮疲于奔命!”
夏元让霍然站起,沉声道:“诸位心中也明白,我军已然到了十分要紧之时,还望诸位勠力同心,共克时艰!若有不遵命令,擅自妄为者,别怪夏某执法如山!”
众将神情肃然,皆拱手应诺,方各怀心事地朝帐外走去。
却在这时,郭白衣突然道:“元让将军留步,元让将军......”
夏元让停身站住,回头看向郭白衣道:“祭酒还有何事?”
苏凌虽然向外迈步,步子也慢了不少,竖起耳朵听着。
郭白衣淡淡一笑,伸出三根手指,似强调一般道:“虽然计议已定,但白衣这三策包罗万象,变化无常,元让将军回营后,还望多想一想白衣所言,记住......三策!可是三策啊!”
郭白衣不知是无意还是刻意地在三策二字上加重了声音。
夏元让心中一动,缓缓点头道:“祭酒放心,我必好好参详!”
苏凌听在耳中,不由得好笑,暗道,这郭白衣怕也有些过于的紧张了,
以前也未见如此,今日却将这三策二字,说了这么多遍.......真的是啰嗦!
想着,他要了摇头,大步出了郭白衣的营帐。
所有人皆走了,只剩郭白衣一人站在空空荡荡的营帐之中,神情流转,似乎想着什么......
............
白日过去,黑夜无声无息地降临。
整个萧元彻的大营寂静无声,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。
甚至这军营比这夜色还要黑上一些,漆黑得连一丝灯火都透不出来。
深秋初冬的夜,风已然有了些凛冽之意,吹起营中旗幡,无声地左飘右荡着。
中领军营的区域,一处大帐还透着微微的光芒。
营帐之中,身材魁梧的许惊虎正仰躺在一张靠椅之上,双目微闭,似沉沉地睡去了。
面前的书案上,蜡灯已然融了许多,微微的光芒摇曳着,忽明忽暗地笼罩在他的脸上,他的脸看起来,也变得忽明忽暗起来。
而书案的正中,放着一张白纸,上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写,白纸的旁边一只毛笔正靠在砚台上。
也不知过了多久,许惊虎陡然睁开双眼,眼中蓦地放出两道异芒,渗人心魄。
与此同时,他翻身坐起,眼珠不停地转动,似思考着什么。
似乎是主意已定,他一把抓起砚台上的毛笔,极速地蘸了蘸墨,伏案在白纸上刷刷点点的写了起来。
他写得很快,片刻之间,那白纸上已然全是黑色的墨迹。
一
气呵成,他方将笔掷在一旁,拿起那写满字迹的纸,轻轻地呵了两口气,借着烛光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,这才呼了一口浊气,抬头沉声道:“你......进来罢!”
话音方落,帐外响起窸窸窣窣的脚步声,片刻之后,一个精瘦,但脸上透着精明强干的小校走了进来。
那小校看年岁倒也不大,约有二十出头,只见他低着头来到许惊虎近前,恭恭敬敬地拱手道:“属下许耽参见主子!”
许惊虎并不说话,只是拿眼睛缓缓地看着许耽,似审视一般。
许耽见许惊虎不言,也只得低头站在那里。
两个人皆不言不语,大帐之中彷如无人一般安静。
半晌,许惊虎方淡淡道:“许耽啊......你跟着我多少年了......”
许耽赶紧抱拳小心翼翼道:“属下乃是孤儿,父母死于乱世,自五六岁流落街头,被主子带回中领军府,如今已然十六年了......”
许惊虎缓缓点了点头,感慨道:“十六年了啊......一晃而过......人这一生,能有多少个十六年啊......”
许耽不知道许惊虎突然说这些,有什么用意,赶紧道:“若不是主人可怜我,属下早冻饿而死于街头了!只是,属下没什么能耐,怕是主人的大恩,今生难报,只等来世了......”
“不用等那么久......来世的事情......谁
知道呢?”许惊虎忽地截过话道。
他深深地看了许耽一眼,方沉声道:“许耽啊,我问你......你真的想报恩么?”
“想!做梦都想!”许耽闻言,又一抱拳,正色道。
“好!......”许惊虎眼中闪出一丝赞许之色,却仍旧如审视一般地盯着他,沉沉道:“我能相信你么?”
“能!许耽身世,主人都知道,许耽愿意成为主人最信赖的人!”许耽赶紧道。
许惊虎摆了摆手,打断他的话,缓缓道:“报恩可不是嘴上说得漂亮,而是要有所行动......你既想报恩,我这里倒真有一件要紧事,让你去做......你可愿意?”
“主人如有差遣,但凭吩咐,许耽绝不推辞!即使是搭上属下的性命不要,许耽也在所不惜!”许耽拱手道。
许惊虎摇摇头,淡淡道:“那倒不至于......此事与你性命无虞......”
说着,许惊虎拿起那张写满字的纸,当着许耽的面,在烛光下装在竹筒之中,封了封漆,随意地扔到许耽的脚下,方才道:“这竹筒之中,装着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......我要你想尽办法,潜出营去,以最快的速度,赶往灞城,将此信交到笺舒二公子的手上!”
许耽心中一动,俯身捡起那竹筒,小心地带在身上,方又拱手正色道:“主人放心,许耽定然不负主人所托!”
“此事事关重大
,万万不可走漏消息,否则你我必将死无葬身之地......若是途中你被人所察,或者被人擒获......许耽啊,你可知道该如何做么?”
许惊虎说这话时,只探出一只手,挑拨着蜡芯,并不看他,似十分随意。
许耽却是神情一凛,沉声顿首道:“若真如此,耽便将此信吞入肚腹之中,再自戕!绝不连累主人!”
许惊虎缓缓点了点头,淡淡看了一眼许耽道:“你现在军中何职啊?”
“属下无才,只是一名百夫长!”许耽低头轻声道。
“嗯......去罢,回来之后,就做个千夫长罢!”许惊虎说着,随意的摆了摆手,让他退下。
许耽大喜,拱手道:“主人放心,许耽定然将此物亲手交到二公子的手上!”
说罢,许耽再不耽搁,转头朝着帐外走去。
他刚走到帐帘前,许惊虎的声音自帐内传来道:“许耽啊......你就不好奇,那信中写了什么?”
许耽的身形蓦然一顿,并不回头,沉声一字一顿道:“不该问的不问,不该知道的无需知道......这是属下的本份!”
说着,许耽迈步走了出去。
许惊虎眼神奕奕地看着许耽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之中,忽地朝着烛台猛的吹了口气。
刹那间,天地皆黑。
............
无星无月,黑夜无边无垠,翻滚在军营的各个角落。
一个精瘦的人影,借着黑夜的笼
罩,如魅一般,朝着一处偏僻之地极速地移动着。
那身影倏尔闪现,又倏尔融在暗处之中。
过了片刻,营地的最偏僻的东北角落,那精瘦的黑影缓缓地又浮现出来。
他站定在那里,又朝四周警惕地打量了一番,再次隐入黑夜不见。
如此再三,直到确定无人跟踪,他方不再躲藏。
却见他用极其细微的动作轻轻的从怀中掏出一个竹筒,也不知他如何摆弄,竟将那竹筒片刻撬开,抽出竹筒之中一张纸,借着极其暗淡的光,细细地看了起来。
看了许久,不知为何,他拿纸的手竟不受控制地颤动起来。
终于,他看完了纸上内容,竟又从怀中拿出一个与方才竹筒一般无二的竹筒出来,将那纸塞了进去,小心地封好封漆。
接着,他在怀中又摸了一阵,再翻手之时,竟多了一支笔和一张小纸条。
他极速地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,用细线将团成卷的纸系好。
随后,他双手在嘴边一拢。
“啾啾——”空寂的野鸟凄鸣声传了开去。
过不多时,一只看不清楚颜色的小鸟,扑扇着翅膀,缓缓地落在此人的脚下。
那人附下身,用手摸了摸那鸟的鸟首,怪异的是,那鸟不鸣亦不动。
这人方将方才那张系好的纸条系在鸟腿之上,用极低的声音道:“好鸟儿......快去吧!”
那鸟儿在他身边跳了两下,然后一扑扇翅膀,振翅飞向黑夜茫茫之中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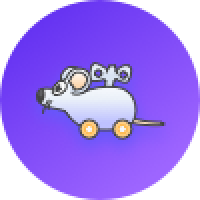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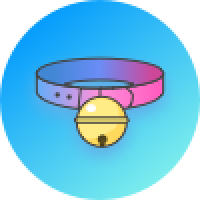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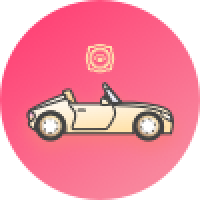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