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承霖眸子微挑:“伯父来夜城了?我是不是得去当面拜见一下?”
付阮:“你这张脸,在家待着吧。”
蒋承霖:“嫌我给你丢人了?”
付阮直直盯着蒋承霖的脸,慢半拍回:“不难看。”
蒋承霖没有马上出声,付阮继续:“我妈说过,看一个人别看上限,看下限,这么狼狈都不难看,那就是靓仔。”
蒋承霖被付阮拐弯抹角夸得心花怒放,两人在厨房里接吻,她选择在家陪他吃饭,要出门的时候,蒋承霖说:“我送你。”
付阮:“不用,下面有人等。”
蒋承霖:“我让许多陪你。”
付阮正在换鞋,闻言,一半玩笑一半认真的调侃:“我去见我爸,你让你的人陪我?”
蒋承霖同样打趣:“敲打敲打伯父,别对一些吃里扒外的人心慈手软。”
付阮第一次没有反驳蒋承霖对付长康的意见,蹬上靴子,干脆利落地说:“走了。”
蒋承霖帮她开电梯,付阮都要进去了,他将人捞回来,捧着脸深吻,完全不顾及头顶的摄像头,付阮没有推开,反手搂着蒋承霖的脖子,在监控里看来,两人指不定谁霸王硬上谁。
站在电梯口,蒋承霖道:“早点回来。”
付阮不紧不慢:“嗯。”
电梯门缓缓合上,她看到蒋承霖笑着对她摆手,刚开始付阮没什么表情,在最后一刻,她止不住笑了一下。
楼下许多在等付阮,亲自把付阮送到小区门口,看着她上了付家车,车边都是付长康身边人,大家统一口径,礼貌叫着:“四小姐。”
家里人对她恭敬,外面人对她畏惧,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,付阮习以为常,像是呼吸喝水,可经过昨晚的事,她不得不重新考量,这到底是理所当然,还是自以为是。
四十分钟后,付阮被带到近郊别墅,再来这里,她本能想到上一次,就是在这,蒋承霖的手被剪刀划得鲜血淋漓。
一路有人开门,付阮走进别墅,换鞋往里走,在客厅看到沙发上的背影,她叫了声:“爸。”
付长康扭头:“来了。”
付阮脱了大衣,递给旁边人,自己坐在付长康对面,茶几上照旧煮着茶,父女二人小一个月没见,两人都很自如,没什么尴尬,只是付长康脸上看得出没休息好的痕迹,毕竟奔六的人了。
付长康给付阮倒了杯茶,付阮主动问:“你什么时候来的夜城?”
付长康:“昨晚。”
付阮刚想说‘那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’,临时想起,她就没开机。
付阮短暂沉默,付长康自顾道:“我让付兆深回来的,他妈肺癌走了,她老家夜城人,想在夜城安葬,我跟付兆深说过,不许找你,没想到你来夜城了。”
“陈敬一那批人,阿醒多余动手收拾,我替你解决了,对你不忠心的人,留在身边也没什么用。”
付阮静静地喝着茶,面色无异,一言不发。
付长康看她杯子空了,提着茶壶递过去,付阮把杯子递过来,付长康一边给她倒茶,一边道:“你有什么想问我的?”
付阮声音如常:“付兆深说周桢死前想见你,你一直都没见。”
付长康淡定喝茶,默认。
付阮:“我是你女儿,付兆深也是你儿子,你不用为我做到这一步,他妈死了,他可以恨我,我不想他恨你。”
付长康没看付阮,但她发现他眼眶很快发红:“我要是怕他恨我,当初就不会连他一起赶到国外,我不见周桢,说实话只有四成是因为你,还有六成,是为了你妈妈,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妈妈醒过来,我都没等到,周桢凭什么想见我就见我?”
长大之后,付阮越发知道成年人的感情,付长康对阮心洁,是爱情大过友情和亲情。他偏执,乖戾,狠辣,甚至六亲不认,他只认他自己的道理,如果那天不是周桢喊阮心洁出去,阮心洁就不会出事。
付阮也是这么认为,就算她找不到直接证据,但她就是知道,阮心洁的死,周桢绝对脱不了干系。
低着头,付长康压抑着愧疚的声音:“这么多年,我始终绕不过这道弯,梦里看见你爸爸,我恨不得藏起来,我没法跟他交代,我怎么跟他说?我把你们母女接到我身边,但我又没照顾好你们……”
付阮的软肋就是付长毅和阮心洁,前者她还来不及保护就没了,后者,她明明可以保护,但最终只剩下漫长无尽的遗憾和等待。
当年撞阮心洁的人,说是癫痫突发,被判了九年多,眼看着明年就要出来了,付阮恨他,但明知他就是替罪羊,她想找周桢要个答案,可是周桢现在也死了,从昨晚到现在,付阮心中无数次涌起的歹毒念头,她想去刨开周桢的墓,看那里面是不是真有她的骨灰。
付阮和付长康对面而坐,两人没有相看,但皆是红着眼眶,良久,付阮抽了纸巾递过去,声音还算平静:“如果没有你,可能我现在胎都投了好几回了。”
付长康接过纸巾挡住眼睛,“别胡说八道,有我在,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手指头。”
付阮:“爸,我跟你商量件事。”
付长康抬眼:“你说。”
付阮:“我想搬到夜城,封醒一个人在这边,他也没有三头六臂,我怕他吃不消。”
付长康一瞬变了脸色:“你想来夜城,不是为了南岭,是想躲付兆深吧。”
付阮面不改色:“陈敬一这次的事给我提了个醒,在大家看来,付兆深从来没做错过什么,很多人跟他的感情,可能比跟我还深,我看不了他,不能逼所有人跟我一样,没必要难为大家,我想来夜城把南岭做好。”
付长康斩钉截铁:“不可能,要走也是他走,我跟他说过,能不能留下,要看你的心情,你不愿意,让他立马从哪来回哪去。”
付阮看着付长康的眼睛:“爸,我们都讲点道理,以前我讨厌他,因为他妈是周桢,现在周桢死了,他还是你儿子,你要是因为我再把他撵到国外去,外面还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把我给淹死?”
付长康阴沉着脸:“我看谁敢说你一句?”
付阮风轻云淡:“爸,我不是十七岁了,这些年我也想了很多,比如付兆深是不是无辜受牵连,你跟亲儿子分开八年,你无不无辜?冤有头债有主,谁的错谁买单,我不恨付兆深,你让他留在国内。”
付长康沉吟半晌:“谁也别想把你撵走,你要是不介意他回来,就让他回来,但你必须留在岄州,我还指望你给我养老呢,你哪都不许去。”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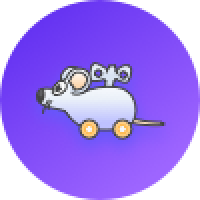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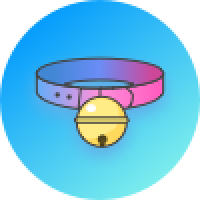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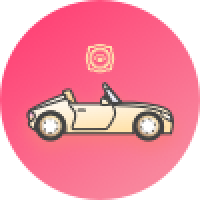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