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承霖没戴眼镜,干干净净,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,唯独那张付阮亲过无数次的嘴,此时左边嘴角红肿,明显能看到一条一厘米长的深红色伤口,是被拳头硬生生打裂的。
蒋承霖身后,一左一右,站着小龙和许多,付阮脸色阴冷,用尽全力克制自己不要转移视线,不要去看小龙和许多,甚至不要去想,到底是哪个混蛋把蒋承霖打成这样。
许多瞧见付阮的眼神,用尽全力控制自己不要转移视线,不要露出鬼祟心虚的表情,蒋承霖答应过他,不会跟付阮说是他打的。
小龙一贯面无表情,像是欠债和追债同时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,他知道蒋承霖和付阮是在演戏,可蒋承霖脸上的伤不是假的,到头来,还是蒋承霖受委屈。
蒋承霖看着付阮,付阮看着蒋承霖,在外人眼中,他们下一秒就会动手,但在他们眼中,蒋承霖知道付阮是心疼到想发脾气。
开口,蒋承霖声音冷淡又讽刺:“什么风把付四小姐给吹来了,我不记得我有请过你。”
付阮尽量不去看蒋承霖受伤的嘴角,冷脸回道:“一股腥风,我顺着味道找,没想到船上是你。”
蒋承霖皮笑肉不笑:“看人在海上就说腥风,要不说空穴来风,还得看付四小姐。”
他一口一个付四小姐,是事实,但谁听了都是讽刺,曾经的前妻,后来的女朋友,如今到底又成了前女友,每当有人觉得他们是真爱时,两人总会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:爱你大爷。
都是旧情人见面,难免会红眼,但蒋承霖和付阮见面,那是分外眼红。
付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:“空穴来风不要紧,蒋四公子下一句别说我是欲加之罪就行。”
蒋承霖笑意不达眼底:“我有什么罪?”
不等付阮说,他自顾补道:“哦,之前你怪我买宝康,我说我是合法购入,你忙了一晚上,找到我不合法的证据了?”
蒋承霖当众挑衅付阮,连带着让大家对两人下午见面一小时都说了些什么,展开无限联想,甚至有人觉得,蒋承霖要是这个聊天方式,也难怪付阮会揍他。
付阮聊着聊着,脸色突然变黑:“蒋承霖,有种别这么拐弯抹角阴阳怪气,敢做就敢承认。”
她直呼其名,蒋承霖也收起脸上细微笑意,装都懒得装,冷脸道:“宝康大楼是我买的,就怕你不知道,我差点敲锣打鼓,我拐什么弯抹什么角了?你下午到我公司来找我的时候就知道,现在又突然跑过来,装什么失忆?”
付阮盯着蒋承霖的脸问:“你对付兆深做了什么?”
离得近的人,可以看到蒋承霖气得咬肌都出来了,付阮当着整船人的面质问蒋承霖,还是为了付兆深,这都不是撕破脸,而是根本没给两人复合留余地。
所有人都听得心惊胆战屏气凝神,蒋承霖额角青筋隐现,怒极,一眨不眨地回道:“我就是要让他当丧家犬,你别以为我下午跟你说的话是开玩笑,从今往后,只要在岄州,谁敢跟付兆深做生意,我就当他不想跟我做生意,谁跟付兆深当朋友,就是跟我蒋承霖当敌人。”
说这番话的时候,蒋承霖明显在气头上,说完,他渐渐恢复理智,又变成平日里那副嬉笑怒骂的随和模样,看着付阮,风轻云淡地说:“岄州以外,我能力有限,但只要付兆深还在岄州,我就让他免费体验一下,什么叫举步维艰,芒刺在背,如履薄冰,悔不当初。”
莞尔,蒋承霖总结:“想成功,重新投胎。”
瞧着蒋承霖和付阮当众表演期末大戏,乔旌南脑子里有两个声音,一个在说:【没事儿没事儿,假的】
另一个在说:【不是真生气了吧?感觉付阮下一秒就要掀桌子了】
付阮没掀桌子,只是用冷成冰锥的眼神盯着蒋承霖的脸,毫无预兆地突击审问:“所以车祸也是你做的。”
话音落下,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,蒋承霖不动声色地凝视付阮,没有马上说话。
付阮:“敢做不敢认?”
蒋承霖冷脸,一言不发。
乔旌南从旁道:“东西不能乱吃,话也不要乱说,这里这么多人都能作证,承霖一直都在船上。”
付阮目不斜视:“我有说他亲自开车撞的人吗?”
乔旌南腰杆子一挺,十分不爽:“你看看你手机,船上屏蔽信号,我们下午六点多就上船了,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儿。”
付阮:“知不知道和做没做,没有因果联系。”
乔旌南瞪眼,蒋承霖先一步开口,声音淡到极致:“不用跟她解释,有些人生来自大,永远觉得自己想的就是对的,她觉得对的不是真相就是真理,她今天说我找人撞付兆深,谁敢替我说话,谁就是她下一个眼中钉。”
平静说完,蒋承霖看着付阮,无波无澜:“你为付兆深来找我,第二次。下午的时候我还在想,大不了以后老死不相往来;现在我改主意了,从今往后,我们互为眼中钉,谁也别放过谁。”
“承霖…”乔旌南本能拦了一句,没办法,心里揪得慌。
蒋承霖没等付阮的回答,起身,大步往外走,乔旌南,小龙,许多和蒋家保镖,一堆人紧跟其后。
明明是蒋承霖组的局,明明是他的船,可最先离开的人,也是他。
再后来,付阮也回到隔壁游艇上,消失在众人视线里。
蒋承霖和付阮,终于有那么一丝丝求而不得因爱生恨的既视感,整个二层算上保镖,百十来人,但凡谁出去说一嘴,哪怕不用添油加醋,也绝对是开年绝世大场面。
……
小游艇上,乔旌南和蒋承霖刚进一层客厅,前者忍不住,谨慎问道:“你刚才不是真生气吧?”
蒋承霖走在前面,闻言一转头:“你不是知道我俩演的吗?”
乔旌南表情立刻从紧张到无语,心跳还不稳,他半晌没出声。
蒋承霖坐在沙发上,让人打听付兆深出了什么事,许多出去一圈,再回来,把晚上车祸两死两伤的消息一说。
乔旌南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他看向蒋承霖:“不是你找人做的吧?”
蒋承霖回以他一记‘别说疯话’的眼神。
乔旌南已经凌乱了:“就你刚才跟付阮说的那些话,你现在上岸杀了付兆深我都信。”
蒋承霖一句话点名局势:“有人想浑水摸鱼。”
乔旌南迅速整理心情,运动之前差点被吓坏的脑仁儿,几秒后道:“两死两伤,这么严重,会是付长康的苦肉计吗?”
蒋承霖:“死老头要是不想要付兆深活,就不会让他回岄州,他没有虎毒不食子的良心,但他也找不到长生不老的药方,在他心里,付兆深应该是他最中意的继承人。”
乔旌南顺着推测:“如果不是付长康,付兆深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,那就是背后还有人,一直在盯着蒋付两家的一举一动,见缝插针想让你们往死里斗。”
蒋承霖:“后半句没问题。”
乔旌南看向蒋承霖,后知后觉:“……你怀疑付兆深有自导自演的可能?”
蒋承霖:“不是谁都像我这么惜命。”
乔旌南沉默半晌后说:“也是,只要动力足够强,你还不是心甘情愿让人把脸打破相?”
蒋承霖靠在沙发上,不紧不慢,细细梳理:“从有人故意挑拨付戚两家开始,我跟阿阮就都觉的,别把眼光放的太窄,除了付长康和赵家,或许还有其他隐藏在暗处,希望借明面上的棋子互斗,斗的满盘皆输,最终那人出来收拾残局的可能。”
乔旌南也不糊涂:“所以你跟付阮必须要闹,还得每一步都闹到点子上,之前你们闹,能看出付长康的态度;这次你们闹,就能暂时排除付长康在背后使坏的可能;或许是付兆深自导自演,或许是其他人,只要你们试地够准,往后谁黑谁白就会更明显。”
“如果还有背后人,随着你们各路人越来越警惕,他能从中作梗的机会就更少,所以那个人也不可能一直躲在暗处,他早晚都得出来。”
蒋承霖靠在沙发上,若有所思,又很清醒:“你说我跟阿阮结婚的时候,穿绿色西装还是黑色好?”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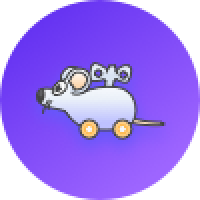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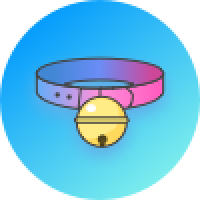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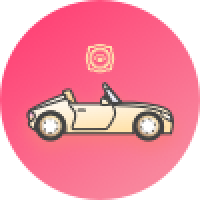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