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超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:“付姿呢?”
谢施与:“她在休息。”
蒋超右眼皮控制不住地弹了一下,脑中本能出现付姿躺在床上的画面,他不敢细想,只拉着脸道:“让她接电话。”
谢施与声音平和:“安良大厦着火,她在家睡觉呛了烟,我把她送到医院,她刚吸完氧睡觉,有什么事儿等她起来再说吧。”
轻描淡写的几句话,蒋超听得心惊肉跳,蹙眉,问:“她没事儿吧?”
谢施与:“火灾很大,很多人都有些一氧化碳中毒,她不算最严重的,但也要住院观察。”
不等蒋超说话,电话里传来其他人说话的声音,像是护士:“注意你的伤口愈合前都不要碰水,最近天热,还要注意通风,别感染了。”
谢施与:“谢谢,刚才医生嘱咐过了。”
蒋超闻言,脑中很难不脑补出诸多画面,比如谢施与为什么会出现在安良大厦?他是现赶过去英雄救美的?还是事发当时,他就在付姿家里?可他刚刚还说,付姿在睡觉。
蒋超心很烦,这股烦躁不仅来源于付姿的手机是谢施与接的,更因为参与整件事的人不是他。
还真应了蒋承霖的那句话,房子着了,他在坐牢,鞭长莫及。
蒋超沉默,谢施与主动道:“你找阿姿有什么事儿吗?”
蒋超本就在气头上,听到阿姿二字,更是一瞬恼火:“我找她关你什么事?”
谢施与微顿,紧接着不急不缓:“不关我的事,我只是告诉你,阿姿短时间内不方便接你电话,如果你有急事儿,可以找其他人办。”
蒋超从谢施与的话中,听到了浓浓的……
“你在命令我吗?”蒋超脸色全黑,声音低沉又危险。
谢施与不冷不热:“命令算不上,通知。”
蒋超翻脸:“你算老几?”
谢施与似乎从鼻子里出了口气,类似无奈,但更像无语:“蒋超,我跟你不熟,没义务接受你的负面情绪,你给阿姿打电话,我知道你跟阿姿是很好的朋友,怕你有急事儿找她我才接。”
说着,谢施与微顿,随即道:“但现在看来,你也没什么急事儿,那就挂了吧。”
蒋超黑脸道:“你在追付姿?”
谢施与顿了一秒,出声回道:“我挺喜欢阿姿的。”
他风轻云淡,蒋超后牙咬烂,果然,打从第一眼见谢施与,蒋超就看出这厮目标明确,有备而来。
沉默两秒,蒋超又问:“你们在谈恋爱?”
谢施与淡淡:“还没。”
蒋超刚准备露出嘲讽的脸,心想付姿不会答应,谢施与又说:“我喜欢阿姿,但我还没开始追她,我们认识时间不长,还是先从朋友做起比较好。”
蒋超得意还不到三秒,脸一翻,沉声道:“明明喜欢还做个屁的朋友?”
他本意想讽刺谢施与耍手段,如果谢施与上来就追付姿,付姿不会同意,可他竟然打着做朋友的旗号,就付姿那种人,蒋超太了解了,只要别人不提,她不会上赶着捅穿,生怕自作多情。
结果谢施与淡定反击:“你不也在跟阿姿做朋友吗?”
蒋超心里猛然一翻,血液上涌,指尖是凉的,脸是烫的,不等他回应,谢施与又问:“还是我会错意,你对阿姿就是纯友情?”
心里一浪高过一浪,蒋超拿着拘留所的电话,越想反击,人越懵,嘴都张不开。
谢施与等了半晌,声音如常,自顾自地道:“等阿姿醒了,我会找机会跟她表白。”
蒋超心里翻地太狠,脑子一片空白,想都没想,直接道:“她不会同意。”
谢施与淡笑:“你怎么知道?”
蒋超强弩之末,脱口而出:“我说不行,她就不会答应!”
谢施与直接笑出声,一个字没说,但极尽讽刺。
蒋超真想问问谢施与在哪,他现在就过去,当着谢施与的面,看看他还敢不敢这么猖狂。
可蒋超出不去,警局不是蒋承霖开的,更不是他开的。
咬牙,蒋超不仅仅是愤怒,而是绝望,他甚至不恨谢施与,只恨自己,这种强烈地后悔感,他年少时体会过一次,往后的很多年,想起那些令他后悔的事,他都会在脑中疯狂想象,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做,如果当初没发生…
如果再见面,他一定让念念不忘的人知道,他有在改,有在变,能不能当做以前的事情没发生?
他没有后悔药,又妄图坐时光机,蒋超发现自己钻进了死胡同,以为证明现在的自己跟那时的自己不同,大家的痛苦就都会烟消云散,可实际上,余柠要的根本就不是他的道歉,更不是他的改变,只希望再也不要见。
而他‘证明’了这么久,到头来也不过从侧面证明,他真的无可救药,他只会以伤害身边人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,一意孤行,一厢情愿,一误再误,最后,一拍两散。
他再也回不到十七岁的那年,也回不到三个月前,因为他一个人,让太多人不开心,他以为他在弥补,可他又在不停制造新的后悔,像是坠入一个无尽深渊,没有底,只能不断重复恐惧。
蒋超拿着电话,短暂忘记对面人是谁,直到谢施与开口说:“其实我挺看不起你这种人的,你把阿姿当什么?她在你身边的时候,你把她当朋友,明目张胆去对别的女人好,等到她身边有人追,你又说不可以,你凭什么?你算老几?”
谢施与就差说蒋超占着茅坑不拉屎,蒋超也明明有无数种可以回击的话,可话到嘴边,他就是死都说不出来。
谢施与:“你要还是个男人,就别搞脚踩两条船那套,不喜欢就别芶搭,是个人就更不要跟她说,让她等你出来,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,哪怕你心里还有其他想法,只要你还记着她的好,放了她吧,阿姿那么好,你配不上她。”
说完,谢施与径自挂断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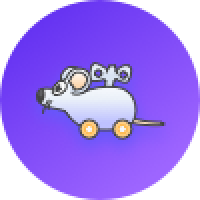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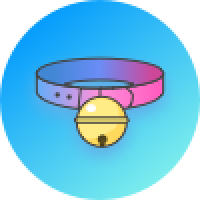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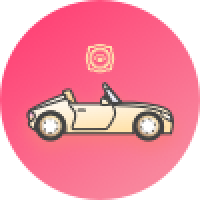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