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狐狸的头在封醒小腹右下方,这个位置已经很低了,蒋承希满眼惊讶,目不转睛地看着,而后发出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:“只有颗狐狸头吗?”
封醒言简意骇:“还有。”
蒋承希真诚:“在哪儿?
”封醒:“想看吗?”
蒋承希不摇头了,改成点头如捣蒜,这不废话嘛,什么事都讲究个有头有尾,她倒要看看,藏得这么深的小狐狸,尾巴还能甩到哪里去。
封醒没想这么早就给蒋承希看,但来都来了,择日不如撞日。
握着蒋承希的手,封醒把宽松的病号服裤子,又往下褪了几公分,这地儿总共就这么大,蒋承希很快就瞥见不该看的东西,脸红没红不知道,但她心跳如战鼓,掌心瞬间发烧。
封醒也很紧张,他不确定蒋承希会不会喜欢这个礼物,两人一个脱一个看,正全神贯注时,病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,蒋承希头都没回,做贼心虚到极致,抓着封醒的裤子,用力往上一提。
封醒面对门口,他第一眼先看到付阮,紧接着看到付阮身后的蒋承霖。
蒋承希正在给封醒盖被子,付阮眼尖,她显然看见不该看的画面,不由得眼带询问。
蒋承霖比付阮少看见提裤子的一步,他只看到蒋承希给封醒盖被子,可饶是如此,他心里还是诸多想法。
病房里有空调,并不热,没事掀什么被子?主要真是热的话,干嘛一听到开门就盖被子?
被子里藏什么宝贝了?
付阮跟封醒是兄弟,加之蒋承希也讨喜,她看破不戳破,声音如常:“怎么样了?”
封醒面色如常:“没事”
付阮早就听闻封醒撑到手术室,也要告诉医生‘个把礼拜’的壮举,明目张胆地开涮:“个把礼拜能下地吗?”
封醒也不甘示弱:“少见你,可以好的快点。”
蒋承希手忙脚乱,搞得自己脸都红了,硬撑着打招呼:“嫂子,哥。”
蒋承霖越发怀疑,封醒到底怎么蒋承希了?
别说中了枪伤等同上了保险,男人这辈子除了躺在盒里,就没有确定保险的时候。
蒋承希受不了蒋承霖审视的目光,出声道:“你们先坐,我出去给你们拿点儿喝的。”
封醒目光追随蒋承希,直到她出门,付阮坐在床边椅子上,问:“怎么没用止疼棒?”
封醒:“用不着。”
沙发上的蒋承霖闻言:“这种时候就不用攀比了吧?”
封醒:“我不用也不会躺在床上哼唧。”
这话就差直接报蒋承霖身份证号码,付阮出声道:“耐疼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技能。”
封醒直揭付阮老底:“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比?”
付阮微顿,紧接着一眨不眨地回道:“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蒋承霖:“别不是承希在这,你有包袱,不好意思用吧?”
封醒面不改色,舌战这俩贼夫妻:“有棒棒糖,谁还用止疼棒?”
蒋承霖一瞬噎死,蒋承希的甜在蒋家是出了名的,就连蒋超都会在蒋承希面前当个好哥。
三人斗了一圈嘴,付阮和蒋承霖联手都没在封醒这里讨得便宜,封醒先把话题扯回正道:“现在你俩的关系暴露了,付兆深就算不知道蒋承彰身边有我们的人,他也知道你不信他。”
付阮神情淡漠,口吻如常:“他从来没想过拿真心换真心,不过在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。”
封醒看着付阮,付阮兀自道:“付长康承认了,是他害的我爸,但他不承认害了我妈,说是周桢做的。”
封醒知道,付阮一直在等这一天,哪怕很多人都已经确定就是付长康所为,可要他亲口承认,是付阮唯一的目的。
现实远没有电视里演得那样,多年冤案终有罪证,凶手难以辩驳只能认罪伏法,如果有证据,蒋承霖不会找了这么多年都一无所获,付阮也不会掘地三尺却无功而返。
全世界能证明付长康就是凶手的人,死的死伤的伤,除非他自己,否则这件事无解。
外人会觉得付长康死了就好,至于怎么死的,又有什么分别?
可对付阮而言,付长康可以有一万种死法,但他最该死在对付长毅和阮心洁的忏悔当中。
不是付长康不死,付阮不能安眠,而是付长康不说出当年真相,付阮会带着愧疚,终生难忘。
蒋承霖:“付长康已经重新被警方和检察院接手,昨天混在天水楼里开枪的那两个人,愿意指证是付长康买凶杀人。”
封醒眼底透出几分精明:“你出了多少?”
蒋承霖面色坦然:“亡命徒爱财,但也不会拿命去拼,除非想给身边人留点什么,我只是找到他们两个的家人,保证付长康的人不会碰他们。”
封醒没说话,只眼底露出惺惺相惜的欣赏之色,蒋承霖也没说话,满眼都是‘一般一般,正常操作’。
付阮受不了两人无声的护捧臭脚,不苟言笑的说:“付长康一时半会死不了,还有蒋承彰和付兆深,事还没完呢。”
谁料蒋承霖和封醒异口同声:“不用怕。”
付阮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培养出的默契,难道这就是互为大舅哥的心意相通?
眉头轻蹙,付阮道:“谁怕了?”
封醒:“也不用急,快点年底,最迟明年,一定让你去蒋家提亲。”
蒋承霖可听不得这话,唇角不受控制地勾起,翘着腿坐在沙发上:“这事都知道了吗?”
封醒:“到时候我跟她一起去。”
“好…”蒋承霖正想说欢迎,话一出口就琢磨出不对味来,脸上笑容逐渐消失,瞥着病床上的人道:“你来我们家,想压轿,还是想近处看个热闹?”
封醒回:“你嫁,我娶。”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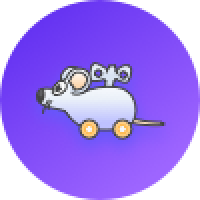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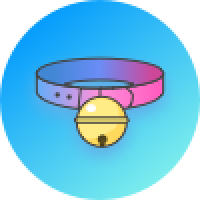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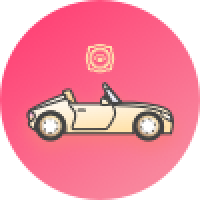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