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木绯见封炎没披斗篷,小声地问了一句:“你不冷吗?”
封炎觉得连脖子都开始烫了,摇了摇头。他非但不觉得冷,还觉得热呢,抬手扯了扯领口。
呼啸的寒风一阵接着一阵,心神不宁的众人都渐渐地冷静下来,慕祐昌和慕祐景目光复杂地看着前方的皇帝和岑隐。
刚才的地动来得实在太突然,很显然,在父皇这边,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。
那么……
兄弟俩皆是心念一动,想到了同一个人,目光都朝同一个方向望去。
几步外,着一件梅红色百蝶穿花刻丝褙子的耿听莲正站在耿夫人的身旁,纤细窈窕的身形在寒风中显得尤为娇弱可人。
二皇子慕祐昌抬起腿,想过去安慰一下耿听莲,然后才抬起的右脚下一瞬又收住了,耿听莲的身旁已经多了一道颀长挺拔的身形。
“耿五姑娘。”
慕祐景清越的声音把失魂落魄的耿听莲唤醒过来,她怔了怔,目光从岑隐的背影上收回,循声看向了慕祐景。
慕祐景只以为耿听莲是被刚才的地动吓到了,神情变得愈发柔和,劝慰道:“耿五姑娘,你别怕,已经过去了……”说着,他又对着一旁的一个內侍招手道,“还不赶紧替耿夫人和耿五姑娘去取两件斗篷来。”
耿夫人听着心里颇为受用,看向慕祐景的眼神中就多了一丝满意。诸位适龄的皇子中,二皇子已经娶了皇子妃,四皇子年纪太小,也就是说,剩下的人选只剩下了大皇子和三皇子。也不知道女儿的心意如何……
耿听莲这半月来一直是京中瞩目的焦点,三皇子慕祐景与她站在一起,自然也就吸引了不少人微妙的目光。
他这位三皇弟的心思,那可谓是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啊!后方的慕祐昌盯着慕祐景那俊朗的侧颜,瞳孔变得越来越幽深,心里冷哼着。
慕祐昌眸光微冷,心中飞快地权衡了一番,就有了答案。
“语儿,”他温柔地扶住了楚青语,嘘寒问暖,还仔细地替她扶了扶七翟冠上略有些歪斜的金簪,“你没受惊吧?”他看着楚青语的眼神温和似水。
其实昨天楚青语就已经告诉了他今天会有地动,只是他因为千枫寺的事对她有所疑虑,然而今日的事实证明了一切,楚青语的预知梦是真的……他错了,他不应该因为这些日子的不顺就怪到楚青语的身上。
便是耿听莲是天命凤女又如何?!
他还有楚青语,还有楚家,这场夺嫡之争中到底谁胜谁负还不好说呢!
“殿下,妾身没事。”楚青语抬眼看着慕祐昌温柔斯文的脸庞,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
今天的地动想来足以挽回慕祐昌对她的信心,她对未来的所知对于慕祐昌而言,那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无价之宝!
天命凤女……
楚青语眸光闪了闪,不动声色地看向了耿听莲。对于她和二皇子而言,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机会。
虽然她早就想试着与耿家搭上关系,但是卫国公府此时还气焰太盛,恐怕是根本不会轻易站队,也不会随意接受一个皇子的示好。
总要让耿海先受点教训,才知道何为雪中送炭,何为强强联手!
她一定会让封炎后悔的!
楚青语唇角微翘,如同一个最温柔贤惠的妻子一般理了理慕祐昌的衣襟,一派鹣鲽情深的样子。
不知不觉中,太极殿前陷入一片寂静,四周只余下了呼呼的风声。
“呱呱!”
一只乌鸦忽然展翅从太极殿的屋檐上掠过,又引得众人一阵心惊肉跳。
乌鸦自古以来都被人视为不祥的象征。
这大过年的先是地动,后又是鸦鸣,也委实让人觉得不吉利。
望着乌鸦飞走的方向,一个中年大臣嗫嚅着出声道:“孙真人说,国有难,才有凤女天降,果真如此。孙真人真是活神仙啊!”
在场的人大多曾听闻过孙真人的种种事迹,不禁神色有些微妙。
子不语怪力乱神,不少的文臣原本对这位什么孙道姑还是有心怀质疑的,此时此刻想着方才的地龙翻身,有的人不禁动摇了……
四周起了一片骚动,众人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着。
耿海心念一动,这是个机会。
自打出了“天命凤女”的事后,耿海知皇帝一向多疑,所以一直没有对此有任何表态,但是现在,地龙翻身应了孙真人的预言,那么皇帝是不是该好好考虑“凤女”一事了。
想着,耿海的心跳砰砰加快。
他上前了两步,试探地对着皇帝道:“皇上,大年初一地动,天降灾祸,乃国有不宁之象……”
皇帝慢慢地转着拇指上的玉扳指,面沉如水。
周围的众人也听到了耿海的这番话,不禁若有所思,私议声愈发响亮了。
又有一个发须花白的老者开口道:“皇上,国有不宁,是不是该去太庙祭祀?”
按照大盛朝的规矩,一旦朝堂内有什么重大的天灾**,皇帝是要去太庙向祖宗告罪的。
大盛朝这百余年的历史中,英宗皇帝因为豫州闹蝗灾,睿宗皇帝因为南方暴民起义,都曾亲往太庙告罪。
众臣纷纷跪下,一下子四周就矮了一片。
耿海带头道:“请皇上亲往太庙祭祀!”
“请皇上亲往太庙祭祀!”
皇帝心里本就七上八下,脑海中如走马灯般闪现许许多多的往事,最后一幕定格在了皇兄引刀自刎的那一幕。
皇帝紧紧地捏着玉扳指,许久许久,才出声允了,心里下定了决心。
“摆驾太庙!”
随着一个小內侍尖锐的嗓音响起,整个皇城都动了起来,数以千计的禁军训练有素地出动了,护送皇帝以及众人浩浩荡荡地从皇城端门而出,一路往东,又穿过太庙的三重围墙,才来到了太庙中央的前殿。
太庙有三大殿,前殿是其中最恢弘的殿宇,殿外雕刻有龙纹、狮纹的汉白玉石栏石台环绕,屋檐上的黄色琉璃瓦哪怕是在阴沉的天空下依旧明亮通透。
殿外还有两排古柏,树龄多是超过百年,苍劲挺拔,蟠虬古拙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。
太庙是皇室的家庙,普通人自然是没有资格进去的,皇帝带着几个皇子以及几位宗室王公进去了前殿,众臣子和命妇们都跪在在外面冷硬的汉白玉地面上,全部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。
自己的膝盖今天可真受罪啊。端木绯默默地心道,天太冷,她连瞌睡都打不起来,只能无聊地数着那汉白玉护栏上到底刻了多少尾蟠龙。
无论是前殿外,还是前殿内都是静悄悄的。
皇帝跪在厚厚的蒲团恭敬地上了香,目光直直地看着正前方。
木制金漆的神座上放着历代皇帝和皇后的牌位,太祖、太宗、英宗……其中某一个牌位便是先帝仁宗皇帝。
皇帝的视线在那个写着“仁宗皇帝”的牌位上凝固了,眼神幽深,身形僵硬。
本来放在父皇旁边的应该是皇兄的牌位,但是现在……
即便他有万般理由,却也终究脱不开“弑兄夺位”之名。
皇帝的眼睫微微扇动地两下,对自己说,他没有做错,是他带领大盛朝进入最繁荣昌盛的盛世,将来他在史书上必能留下浓重的一笔。
为了大盛江山,为了成就大事,有那么一点点小牺牲又算得了什么?!
况且,他也没有对安平他们赶尽杀绝,就连安平的儿子他也百般施恩。他自认已经仁至义尽,列祖列宗又怎么会怪他呢!
皇帝的眼神渐渐又变得坚定起来,他正想起身,忽然就发现上方的牌位似乎颤动了一下。
一开始,他几乎以为是自己眼花了,但紧接着,就看到神座上的那些牌位都摇晃了起来,发出“咯嗒咯嗒”的声响。
他的膝盖下清晰地传来了地面的震动感,皇帝脸色煞白,心里清晰地意识到,又地动了。
皇帝浑身微微颤动着,连他也不知道颤抖的是地,还是他自己。
“皇上小心!”
一旁的岑隐急忙上前了一步,把皇帝从蒲团上扶了起来。
皇帝神色怔怔,三魂七魄似乎是掉了一半,感觉眼前一阵天旋地转,沉香木的梁栋、金漆神座、笾豆案、两排烛火等等都在晃动着,晃得他头昏眼花,心神恍惚。
“啪嗒啪嗒……”
不知道哪个牌位第一个倒下,撞得其他牌位也七零八落地歪倒在神座上,一片狼藉。
皇帝的身子仿佛被冻僵似的,动弹不得,心里浮现一个念头——
太祖太宗……还有父皇是在怪自己呢!
皇帝心中似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,犹如暴风雨夜的海面般咆哮不已,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
“皇上,殿内危险,臣扶您出去吧……”岑隐轻声道。
然而,皇帝充耳不闻,一动不动,脑海中混乱如麻,往事再次闪现在眼前,想起他的父皇,他的皇兄,他的皇嫂……
须臾,四周渐渐地平静了下来,地动停止了。
几个皇子这才过神来,紧张地跪行到皇帝跟前,七嘴八舌地嘘寒问暖:
“父皇,您没事吧?”
“父皇,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,您还是赶紧出去吧。”
“父皇……”
周围一片喧哗嘈杂,皇帝始终面无表情,眼神阴沉复杂地看着那些歪倒的牌位。
殿内殿外,皆是一片惊魂未定,跪在外面的众臣命妇东倒西歪,不少命妇都是合掌置于胸前,虔诚地闭眼,念佛声不断。
短短一个时辰内,连着两次地龙翻身,怎么想都是不祥之兆,怕是上天马上要降下灭顶之灾,亦或是朝堂、江山有什么**?!
众人心里惊疑、惶恐、忐忑、担忧等等的情绪皆而有之,心口更是沉甸甸的。
这种不安的情绪仿佛会传染一般,空气越来越压抑,天空中的阴云似乎又更浓密了,仿佛有一场暴雨即将降临……
等端木绯和端木宪回到府里的时候,已经是申时了。
“蓁蓁,你没事吧?”端木纭闻讯就匆匆赶到了仪门相迎,拉着妹妹的小手东看西瞧,一脸后怕的样子,心里觉得妹妹当时肯定是吓坏了吧。偏偏当时妹妹在宫里,自己不在她身旁……
“姐姐,我没事。”端木绯笑眯眯地对着端木纭转了个圈,裙摆随之翻飞如蝶,轻盈可爱。
端木纭总算是安心了不少,但还是牵着妹妹的小手。
端木宪看着姐妹俩,满意地捋了捋胡须。今日地龙翻身,天有异象,端木纭又年纪小,端木宪也曾担心她压不住,府里出什么乱子,但回来一看,府中一切井井有条,下人们也都举止得体。
端木宪心里很是欣慰,他这个大孙女管家就是稳妥,性子也稳重,哎,这么好的孙女,京中也挑不出几个,怎么她就是不乐意嫁人呢?!真愁人啊!
“纭姐儿,四丫头,你们随我去一趟书房吧。”
端木宪把姐妹俩都叫去了自己的书房,又让人把端木珩也叫来了。
祖孙四人在书房里坐下了,端木绯今天在宫里好一阵折腾,正口渴呢,埋头喝起茶来。
“纭姐儿,府里的情况怎么样?”端木宪第一个问端木纭道,神态十分慈爱,“有什么事你不好处置,尽管与祖父说。”
“祖父,一切都好。”端木纭不紧不慢地道来,把从正午第一次地动后的处置一一道来,比如她让府里的下人把所有院落包括佛堂、厨房的烟火都熄了,让大家紧闭门户以免让宵小钻了空子,又让一府的主子奴婢都聚集在仪门前后比较空旷的地方,特意按照名册点了名等等。
等第二次地动后,又过了一个半时辰,见没再出什么事,端木纭就让各房都报了有没有人受伤和有没有东西损坏,也都是些小事,二房摔了个瓷瓶,三房摔了两个杯碟,厨房里洒了锅热汤,幸好没烫伤人……
端木纭把这些损失都算在了公中,又吩咐下去晚上给府中上下都加菜压压惊,且恩威并施地赏罚了一番。
有的人平日里平平顺顺的看不出个好歹,倒是借着今日这一乱,端木纭看出了哪些人得用,哪些人只是花花架子。
端木宪听着偶尔应一声,频频点头,笑容更深了,心里想的是以后孙长媳务必要找个像纭姐儿这般得力的,万万不能再寻像小贺氏、唐氏这种乱家的媳妇。
不急,先等长孙过了秋闱再说。
端木宪的目光从端木纭、端木珩身上一一掠过,最后停在了端木绯身上,端木绯刚喝完了一杯茶,又吩咐丫鬟去添茶水。
“四丫头……”看着小丫头没心没肺的样子,端木宪的神情更复杂了,开门见山地问道,“你可是早就知道了?”
今日在太极殿第一次地动时,端木宪看到不远处的一盏宫灯倒了,便想起宫宴前,端木绯特意让一个內侍把他旁边宫灯搬走。端木宪是聪明人,一下子就悟了。
端木绯一边端起新的茶盅,一边点头道:“天象显示彗、孛犯天市,京城必有地龙翻身。”她的话音消失在樱唇与杯沿之间。
“……”看着端木绯一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,端木宪难免心生一种一言难尽的心累,耐着性子又问道,“四丫头,你怎么不告诉我?”
端木绯抬眼看向端木宪,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安抚道:“祖父,从天象来看,这次只是小小的地动,也就是稍微晃几下而已,没什么大碍,不会有天灾**之忧。”
“就算祖父禀明了皇上,就连钦天监都没瞧出来会有地动发生,皇上可会相信?”
“而且,近日雪灾、战乱之祸,皇上已经忧心忡忡,祖父无凭无据,跑去跟皇上说要地龙翻身,只会惹得皇上不快。”
“哪怕有今日可以证明祖父没说错,皇上的心里也会梗了一根刺。”
“既然如此,又何必要知道呢?”
端木绯有条不紊地说着,说得她又口干了,又去捧茶盅,看着碧绿的茶汤里沉沉浮浮的茶叶,心想:若是真有严重的地动,她肯定会说的,不管有没有人相信。
人生在世,但求问心无愧。
端木宪垂眸沉思,当皇帝还是皇子时他就在朝堂上了,对于皇帝的性格再了解不过,四丫头所言不错,他要是知道了,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,还不如不知道。
想着,端木宪看着端木绯的眸子亮了起来,心里叹道:四丫头怎么就这么聪明呢!
端木珩听着也是面露沉吟之色。
“四丫头,那接下来……”端木宪有些迟疑地问道,也不知道自己想听到什么答案。
“祖父放心,接下来不会再有地动了。”端木绯笑吟吟地说道。
端木宪的心总算是落地了:那就好!
“纭姐儿,四丫头,你们俩乖乖留在家里,还有珩哥儿,你也干脆在家里读书,没事别出门了。”
端木宪叮咛了一番后,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虽然今天的地动极其轻微,应该无碍,但端木宪身为首辅还是有得忙了,尤其要看看京畿附近有没有伤亡,无论如何,朝廷总要对百姓摆出个态度才能安抚民心。
端木珩、端木纭和端木绯也跟着端木宪出了外书房。
天空还是一片阴云密布的景象,端木珩与姐妹俩道了别,回了晨风斋,姐妹俩则手牵着手往后院方向去了。
“蓁蓁,”端木纭晃了晃妹妹的小手,一本正经地叮咛道,“下次你不可以再瞒着我了,”今天地动时,真的把端木纭吓坏了,她不担心自己,她就担心她的妹妹,妹妹比她的命还重要。
“姐姐,我以后一定跟你说。”端木绯忙不得应下,亲昵地挽着端木纭的胳膊撒娇。
今日有地动的事,除封炎外,她就连端木纭也没说,差点连她自己都忘了。
端木纭哪里能真跟妹妹生气,在她小巧的鼻头刮了一下后,就笑了出来。
姐妹俩一边走,一边朝湛清院的方向去了。
这一路,也难免遇上一些丫鬟婆子,纷纷地给姐妹俩行礼,步履还有些虚浮,神态间透着几分惊魂未定的感觉,还不时听到有人说要明后天去庙里拜拜,求个平安符。
端木纭忽然想到了什么,停下脚步道:“蓁蓁,你知道今天地动时府里谁最镇定自若吗?”
端木绯怔了怔,想来想去,除了自家姐姐,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有谁。
眼看着端木绯难得被自己难住了,端木纭噗嗤一声笑了出来,说出了答案:“是团子和小八。”
第一次地动发生时,端木纭正在东次间里,抱起睡在一旁的小狐狸就冲出了屋子,小狐狸当时在她怀里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,那样子仿佛在说,一惊一乍的,这是干嘛啊!
至于小八哥,它似乎以为她们是在玩,乐得上蹿下跳的,与一院子惊魂失措的丫鬟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听端木纭把当时的情景娓娓道来,端木绯也被逗乐了。
她的笑声引来了小八哥,亢奋的小八哥展翅从墙头飞过,稳稳地落在了端木纭的肩头,看着端木绯“坏!坏!”叫了两声,仿佛在质问她一整天野哪儿去了。
端木绯抬手摸了摸它油光发亮的黑羽毛,想到了什么道:“姐姐,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,动物对于灾害似乎有强烈的直觉,它们会比我们人更快地感觉到危险,然后迁徙逃离……也许小八也知道这次的地动根本就不算什么。”
“呱呱!”小八哥仰首叫了两声,仿佛在说,就是这么回事。
看着它没心没肺的样子,端木纭感觉端木绯实在是高估它了,倒是小狐狸没准真的是。唔,自家的团子真聪明!晚上给它多添一只鸡腿。
“大姑娘,四姑娘,”几个丫鬟见两个姑娘回来了,急忙迎了上来,七八个人一起过来,声势赫赫。
虽然地动都过去好一会儿,可是丫鬟们的心还是有些七上八下的,总担心地动还会再来,这种心情难免也表现在了她们的神情与言语之中。
端木绯看看小八哥,再看看紫藤她们,又一次笑了,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散而去。姐姐说的没错,果然还是小八这家伙最是从容镇定了。
丫鬟们面面相觑,完全不知道四姑娘在笑些什么。
不过,看四姑娘这么欢快的样子,她们忽然觉得心定了不少。主子都不怕,她们也没什么好怕的。
“四姑娘,您应该饿了吧?”碧蝉笑眯眯地上前了一步,“奴婢听说在宫宴里人多,根本就吃不上什么好东西,您想吃什么?奴婢这就让小厨房给您去做。”
被碧蝉这一说,端木绯霎时就觉得饥肠辘辘。她今天在宫宴里也就吃了些点心,喝了些奶酒,幸好还和涵星她们一起在宫宴前吃了些烤栗子垫垫胃。
端木绯立刻就报了一溜的吃食,鸡丝面、荞麦皮菜肉馄饨、蜜汁胭脂鹅脯、金丝枣泥糕……
端木纭又加了三四个小菜和点心,院子里的下人们随着两个姑娘的归来而忙碌起来,忙碌反而令她们都有了主心骨,心也就定了。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屋里屋外又点起了一盏盏大红灯笼,照亮四方,一切似乎都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。
一直到天黑,端木宪还没回来,但是端木绯也不担心,该吃吃,该聊聊,该睡睡。
自古以来,就不乏地龙翻身之事,尤其是蜀州一带,不过京城是天子脚下,距离上次地龙翻身也有五十多年了,恐怕此刻京中人心未定,端木宪的事多着呢。
的确,大年初一就遭遇了地龙翻身,上至皇帝,下至百姓,都觉得是不吉利的,偏偏又封笔封印了。
大年初一开笔,那可是大盛朝建朝来是从未有过的事,皇帝自然是不愿破了惯例。
于是内阁承担起了一切,着令统计伤亡和各处的损失,然后再报由司礼监。
这件事说来一句话,实际要动手,涉及的人员可不少,皇帝特意派了锦衣卫和禁军协助,那些相关的官员比如京兆尹、户部、工部等等只好都回衙门办差。
此事关系重大,这么双眼睛盯着,次日也就是大年初二,结果就出来了。
这次地动以京城为中心影响了方圆百里,京畿地区只有轻伤三十二人,大多是因为地震突然来了,被些从架子上滚落的瓶瓶罐罐砸到受的伤,还有一个人是被受惊的马擦撞了一下,伤得最重的一人还是因为过拱桥时忽然地动,他吓得脚软,摔倒了,就从拱桥上骨碌碌地滚了下去,最后左胳膊撞在桥墩上撞折了。有道是,伤筋动骨一百天,这人估计是要养上三个月了。
整个京城巡视下来,既没有房屋倒塌,也没有建筑崩裂,比起之前的雪灾,这次的地动简直不算回事,压根儿不需要“救灾”,倒是给京兆尹省了不少事。
在司礼监的提议下,太医院派出了两名太医去一家家地医治伤者,开方赠药,得到了不少的感恩,直呼什么皇恩浩荡。
虽然没出什么大事,但连着几天京中都有些人心惶惶。
本来大过年的,各家各户都忙着走亲戚、摆席宴、放鞭炮等等,这下,谁也没心思出门了,京城的街头巷尾都空荡荡的,明明正是春节,京城却弥漫着一种萧索的气氛。
倒是京中的各大寺庙、道观的香火旺盛了起来,前去上香的人络绎不绝。
一直到了初四,再也没发生地动,人心才开始安定了下来,京城中的气氛又渐渐地热闹了起来,而端木宪也稍稍缓过一口气。
“老太爷,府里刚送了饭盒来。”长随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红漆木食盒走进了户部衙门。
屋子里点着一个银霜炭盆和一个香炉,暖烘烘的,打开食盒后,空气里就多了几缕袅袅的白气与食物的香味。
白灼芥蓝、茄鲞、野鸡瓜齑、虾仁焖白菜、香菇枸杞鸡汤,四菜一汤,还有饭后的两道点心,只是看着就让人觉得食欲大振,心里再妥帖不过了。
哎,幸好家中的事务都有纭姐儿操持着,他在外头办差才没有了后顾之忧啊。端木宪一边提起筷箸,一边感慨地想着,夹了块虾仁送入口中。
这两天,端木宪在外面也听说了别府的一些情况,有的府邸没看过门户,竟然有大胆的刁奴趁地动时偷了主家的东西潜逃了;也有的人家,没灭了烛火,灯笼不慎倾倒,把一间屋子烧掉了一半;还有的人家过犹不及,吓得干脆举家出京过节去了……
明明就是一个小小的地动,连一枝梅都震不掉,他们就自乱阵脚,最后带来的影响倒是比地动大多了。
还好自家有纭姐儿坐镇。
纭姐儿真是有他这个祖父当年的风范啊,年纪不大,做事沉稳利落,心中有谱。
也就是……
端木宪又吃了块香菇,忽然觉得食不知味,一方面愁着端木纭的婚事,另一方面,又想着要是端木纭出嫁了,这府里可怎么办啊。
要不然,自己还是先替珩哥儿找个媳妇?端木宪魂飞天外地想着,筷箸夹向那碟茄鲞,然后筷箸又在半空中顿住了。
不行,他可不能被纭姐儿给带偏了。
纭姐儿是不想嫁,却不妨碍他悄悄给她相看起来,试想,若是有个年轻俊才如他年轻时那般才学出众、品貌不凡,又能得中状元探花,想必纭姐儿见了一定会改变主意的。
偏偏春闱在明年,明年纭姐儿那可就十七了。
要不,他去和皇帝说说,设法开个恩科?
端木宪心不在焉地吃了小半碗米饭,正打算喝点汤的时候,长随又步履匆匆地来了,禀道:“老太爷,宫里来了人传口谕。”
这下,端木宪也顾不上喝汤了,整了整衣裳后,就即刻往衙门的大门而去。
来传口谕的内侍就等在大门外,见端木宪来了,急切地说道:“端木大人,还请赶紧随老奴进宫吧。”
看那內侍神色紧张,端木宪心里咯噔一下,试探地问道:“王公公,不知皇上……”
端木宪常年进宫,与皇帝身旁服侍的那些个内侍多是相识,王公公也不瞒他,透了点口风,“端木大人,皇上龙体抱恙……”
端木宪怔了怔,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,看来今年开恩科是没戏了。
长随飞快地备好了一辆黑漆平头马车,端木宪连忙上了马车,随王公公一起火速赶往皇宫。
大年初四的街道上,还是空荡荡的,马车一路飞驰,毫无阻碍,没一炷香功夫就抵达了宫门口,还恰好遇到了同样奉诏而来的游君集。
如同王公公所言,皇帝又病了。
自打大年初一折腾了一番后,皇帝就有些心神不宁,又是连着几夜恶梦连连,一晚上反复被惊醒,连太医开了安神茶、安神香也没起到多大效果,如此折腾了几天后,身心俱疲的皇帝终于病倒了。
当端木宪和游君集赶到养心殿时,寝宫的里里外外都是人,二皇子、三皇子和四皇子在皇帝榻边侍疾,五皇子以及下头几位年纪小的皇子就待在外间候着。
几位内阁大臣、耿海、魏永信等天子近臣都陆陆续续地来了,心思各异,众人的目光俱是望着龙榻上的皇帝,脸上掩不住担忧之色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,气氛凝重而压抑,落针可闻。
身着明黄色中衣的皇帝靠着一个绣龙大迎枕坐在榻上,眼下一片青影,甚至连脸颊都微微凹了进去,短短几天内就苍老了好几岁,憔悴不堪,看来与大年初一时判若两人。
端木宪心惊不已,恭敬地给皇帝行了礼。
皇帝挥了挥手,示意他免礼,赞道:“朕听阿隐说,你最近把那些善后事宜处置的不错,很好!很好,有你们这些肱骨之臣,朕就放心了。”他的声音透着一丝沙哑与疲惫。
端木宪飞快地瞥了一眼站在龙榻边的岑隐,受宠若惊地作揖道:“皇上过奖。”
着大红色麒麟袍的岑隐负手站在三位皇子身旁,神情肃然,狭长的眸子深邃如夜空。
皇帝揉了揉满是褶皱的眉心,又道:“等过两日开笔后,暂时就由内阁和司礼监代理朝事,由司礼监根据内阁票拟做最后定夺。”
虽然在过年前,也因为皇帝生病,也曾把政事交给过司礼监和内阁,但是上一次皇帝只是暂停早朝,几位内阁大臣处理重大政事时还是会进宫与皇帝商议之后,再行处置,这一次皇帝的意思就是要全心休养,撒手不管朝事。
皇帝话落之后,寝宫里隐约响起一片倒吸气的声音,其他人都惊住了,尤其是几个皇子。
几个皇子本来觉得父皇应该会让他们其中一人监国的,结果竟然与他们预想得完全不同!
三皇子慕祐景垂首恭立在一旁,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,才没让自己失态。
二皇子慕祐昌不动声色地看了慕祐景一眼,他心里虽然失望,却又觉得由司礼监监国总比让他这个三皇弟来的好。
耿海更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,心底霎时掀起一片巨浪。
唯有岑隐还是云淡风轻,镇定从容,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端木宪愣了一下后,就立刻恭声领了旨:“是,皇上。”
“好。”皇帝满意地笑了,连眉心的郁结似乎都消散了不少。
耿海的脸色更难看了,他本来还指望端木宪作为内阁首辅能站出来反对,没想到端木宪这个老狐狸还真是没有一点文人的清高。
也是,端木宪都能让自己的孙女去认一个阉人做义兄,又能清高到哪里去。
不行,自己决不能坐视岑隐把持了朝政,那以后可就真没自己一点立足之地了!
“皇上,臣以为如此不妥,由岑督主暂理朝政,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。”耿海上前了一步,对着皇帝抱拳道。
皇帝没有说话,静静地三尺外的耿海,目光一点点地变得凌厉起来。
任谁都能看出皇帝此刻心情不悦,其他大臣皆是噤声,有人下意识地看向了岑隐。
端木宪也同样沉默了。
这时,后方传来一阵打帘声打破了原本的沉寂,內侍领着和亲王进来了。
和亲王是皇帝的七弟,听说皇帝抱恙,才匆匆进宫问候,谁想一进来,就感觉这屋子里的气氛很是古怪。
看几个大臣和內侍都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,和亲王就知道肯定没好事,一时进退两难。
哎,自己怎么就来得这么不是时候呢。和亲王一边心道,一边硬着头皮上前皇帝请安,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几句客套的问候之语,比如多多休养、保重龙体云云的话,又笑着夸几位皇侄都甚是孝顺。
“王爷说的是,几位皇子都很是孝顺。”耿海巧妙地接口道,又把话题转了回去,“皇上,臣以为不如从几位皇子中择一监……”监国。
“够了!”皇帝眉宇紧锁,不耐地打断了耿海,心火熊熊燃烧着,眼神如冰。
耿海现在让自己从几位皇子中择一监国,接下来又会如何,是不是就要逼自己择立太子了?!
耿海想让他的女儿做太子妃,想要借此来掣肘自己这个皇帝,未免也想得太美了!
“耿海,你是对朕的决议有所不满吗?!”
“看来朕这些年真是太惯着你了,以致你都敢对朕指手画脚了!”
皇帝破口大骂道,一字比一字响亮,一句比一句严厉,到最后一句,几乎是有些诛心了。
耿海心里咯噔一下,扑通一声跪了下去,道:“臣不敢。”
耿海作出不甚惶恐的样子,恭敬地俯首,他只觉得四周其他人的目光如针一般刺在他身上,感觉仿佛成了一个笑话。
他对皇帝一直忠心耿耿,为了皇帝,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,然而圣心易变,这世上本来就是狡兔死,走狗烹。
皇帝现在是嫌自己碍眼了……
耿海眼帘半垂,目光落在岑隐那大红色的袍角上,那鲜艳如血的颜色映得耿海的瞳孔中一片赤红色,有愤,有羞,有憎,有恨。
和亲王只觉得头皮发麻,心里再次怨起自己来,他啊,真是蠢得没药救了,不但不会找时机,而且还不会说话,他没事提几个皇侄子干嘛啊……皇兄不会以为他和耿海是一伙的吧?!
和亲王紧张地咽了咽口水,坐立不安。
皇帝根本就没在意和亲王,他的目光凝固在耿海一人身上,神情更冷。,“ ”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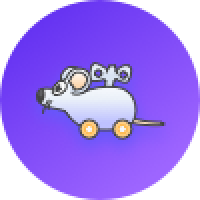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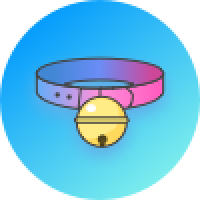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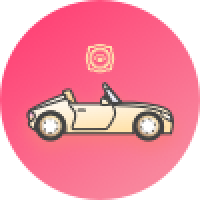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