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算天下女子都不愿意嫁你,我也会嫁你的。”她就那样微微仰了头,小小的脸上已经带着千娇万宠的骄矜。
所有人都当她童言无忌,大概只有他,当了真。
不久后,他就和齐琏出征,战场告捷之后归京,然后发生意外,再然后他成了一只孤鬼,忘了生前的许多,却唯独清晰地记得那日说下那番话的她。
他的庄小浅啊,他怎么舍得放手。
记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,祁严就越来越虚弱了,他再没有离开过义庄,只是躺在以前和庄浅躺的椅子上,拿着那本兵书看着,不远处是齐琏的尸骨,偶尔长欢也会在,大多数时候长欢是不在的抒。
长欢依旧是待在戏楼那里,只是祁严不知道,最近龙兴镇的人都在传,长欢过一段时间就要走了,他不会再唱戏了。
大概是都想再听一次长欢唱的戏曲,这一天,来的人特别的多,阿生和双衣,还有白荷也在,连白阿爹都来了带。
而祁严,是不知道这些的,他还是待在义庄里,看着自己手里的书,没日没夜。
这本书在他死之前其实就已经看过许多遍了的,这么多年来,他依旧一遍又一遍的看着,从不厌烦,这样的书,也不会有厌烦的时候,手边还放着一本小小的话本,话本中间别着一片叶子,那是庄浅上次看到的地方。
她不爱用那些精心制作的书签,反倒喜欢在外面随便捡一张树叶回来,在话本里夹着。
祁严一手拿着兵书,一手搭放在话本上,不时轻轻地摩挲着,偶尔抬起手翻页,搭在书角的拇指已经有些透明了,不时有极其浅淡的白雾消散在空气里,他也不在意,仍旧认真的看着书,目光有时候落在自己的手指上,不知道想起了什么,祁严扬唇露出了一个浅笑。
庄浅踉跄着跑进来的时候,看见的就是这一幕。
“祁严……”她颤着嗓音唤他,话音还没有落下,泪水就已经淌了满脸,她早意识到不好,却未曾想到,跑回来见到他时,他竟已经是随时会消失的模样。
她甚至止不住的后怕,若是自己再晚点醒来,若是自己没能赶回来,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,而他,就这么消散在了这里。
熟悉的声音带着挥之不去的悲伤和不可置信响起,祁严双手一颤,手里的兵书“啪”的一声,掉落在他身上,慢慢的,慢慢的,竟然穿透了他的身体,落在了躺椅上。
谁也没有察觉到,祁严消散的速度在加快。
如果不是庄浅进来后出声喊他,他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她回来了,他已经虚弱到了这样的地步。
“祁严。”她低低的喊了一声,没有丝毫犹豫的跑了过去,而后伸手拥抱他,她怕自己慢上一点,就再也碰不到他了。
可幸好,她伸出去的手没有像那本书一样,穿透过他的身体。
触手依旧是冰凉,却一如既往地让庄浅安心,包括鼻尖已经极淡了的冷香。
祁严在她扑过来的时候,也伸手去抱住了她,将人抱在怀里,黝黑的眸子里,这几天堆积的沉寂才一点一点的散去了,又是一片柔和的笑意。
他轻叹一声,像是牵扯了心脏,头抵着她的额头,轻声问道:“怎么回来了?”
绝口不提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。
“为什么会这样?”可是,祁严不提,不代表真的就这么揭过了,她怎么可能真的不问?
祁严一手伸到她的脑后,抚摸着她的头发,眼底温柔深彻,“你被阿茵带走之后,我醒过来,去那里找你,发生了一些意外,但也知道了很多的事情,我都想起来了,生前的一切,还有……中了失心后忘记的那一切,庄小浅,幸好我那时候没有伤害你。”
是啊,幸好,幸好他即便是忘记了一切之后,仍旧记得不能伤害她,祁严曾无比的庆幸。
“没办法了吗?”她整个人埋进了他的怀里,靠着他的胸口,低低问了一句,声音里小心翼翼的期望让人不忍心打破。
可祁严还是摇了摇头,他轻笑了一声,伸手顺着她的背,上下安抚着。
“别怕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似乎随时都会消散。
可庄浅怎么可能不怕。
胸口的湿润透过衣裳,带着灼烫的温度,烫的他心口忍不住都轻轻地颤抖起来。
“庄小浅,别哭。”他伸手捧着她的脸,让她抬头看着自己,哪怕虚弱,他精致的脸上露出的笑容还是那么好看,好看的……让她更加止不住眼泪。
庄小浅连他指尖的凉意几乎都要察觉不到了。
“祁严……”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,害怕自己一眨眼他就会消失了,伸手急切的去抓他的手,可只有一股细微的凉意从指缝间流过,他在她的眼前渐渐透明。
“庄小浅,回京城等我。”细微的声音像是裹着风,从她的耳边轻飘飘飞过,她只能眼看着他彻底消失,伸出的手什么也抓不住。
冉情一直都站在门口没有靠近,哪怕祁严消失后,庄浅蜷缩在躺椅上,捧着祁严的兵书,哭到失声,像是一只从此失去了庇护的小兽。
长欢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,站在冉情的身边,也没有进去,他们都知道,如今只能让庄浅这么哭一场,否则憋着也迟早要别处病来。
等她哭完了,一些事情她才能听得进去。
庄浅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,哭到后面眼睛已经完全干涩了,后来就睡着了,醒来的时候喉咙一动就疼,眼睛更是肿的有些睁不开。
她还是蜷缩在祁严离开时的躺椅上,四肢僵硬,身上盖着薄被。
冉情看见她醒来,拿了温热的帕子给她净脸,又端了水过来,让她喝了。
似乎哭过之后,一觉醒来,庄浅就将祁严抛在了脑后,她没有再提,也没有问什么,甚至一个字都没有说,正常的吃饭、睡觉、和冉情再一次走上回京城的路,正常的可怕。
这一次,长欢也跟着他们一起走的,义庄第一次的关上了外面那扇大门,只有齐琏,还留在那里,央了阿生他们帮忙看着,等着他们回了京城后带人来取回齐琏的尸骨。
庄浅只带走了祁严那本兵书,她还是喜欢看自己的话本,每次却会将那本兵书放在身边,偶尔伸手摩挲一会儿,而后又继续看着话本,像是……只为了从中得到一些安全感。
离开龙兴镇半个月的时候,长欢坐进了马车,他一开始只是安静的坐着,偶尔看庄浅一眼,看见她神色正常,心里却更加的担心。
“庄浅。”长欢终于忍不住出声喊她。
“嗯?”庄浅将视线从话本上移到他的脸上,应了一声,似乎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
看着她这个模样,长欢又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好说的了,可想到进来时冉情的眼神,他还是将早就想好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“其实清虚子把他师傅找来了,祁严出事之后,清虚子师傅就给祁严看过了,他当时说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,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,却知道祁严一定没那么容易死。”
说的时候长欢的视线一直放在庄浅身上,密切关注着她的反应,说完后又一脸忐忑的看着她。
可庄浅只是很平静的应了一声,“嗯,我知道。”
她看着长欢,甚至扬唇露出一个浅笑,“祁严不会死的,他让我回京城等他,他会来找我的,而且……”她语气一顿,手朝着长欢的方向摊开,手心里苒苒升起一小簇的青火,映着庄浅的眼睛,竟是十分的美丽。
“你看,青火还在,祁严就没事。”她缓缓地笑着,语气里尽是期待,似乎,只要一回到京城,她就能见到她的祁严。
而长欢,在见到那簇青火时就是一脸的呆滞,他后知后觉的想到,这段时间可能真的只是自己和冉情瞎担心的。
庄浅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,收拢了掌心,她笑道:“我知道你们担心我,以后不用啦,我知道祁严没事,就已经很好了。”
长欢最后也终于放下心来,笑着点了点头,钻了出去,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冉情。
说完这些之后,他想了想,还是问了冉情一句:“祁严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事置之死地而后生了?”
冉情眸光闪了闪,轻轻摇了摇头,没有说话。
长欢早就习惯了他的性格,也没有指望从他嘴里听到太多,只是接下来的一路上,他的心情确实放松了不少。
从龙兴镇到京城,走快的,且路上没有什么过多的停留,自然要比庄浅三年前去龙兴镇要快许多,大概一个多月的路程,眼看着已经走了大半。
这日,路过一座小镇的时候,天色已经渐晚,冉情在最大的客栈安排好庄浅,留下长欢,他就出了门,要买明天行路的干粮,顺便打听一些事情。
哪怕只是在这里住上一晚,冉情仍旧会去将镇上的事情打听清楚,以防万一。
长欢和庄浅都知道他是为了万事小心,早就习惯了,也就没有多问。
到了吃晚饭的时候,冉情就已经回来了,什么都没有说,还是长欢忍不住好奇的问起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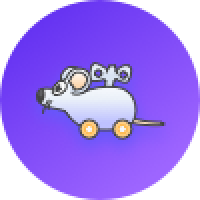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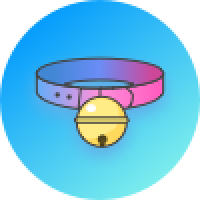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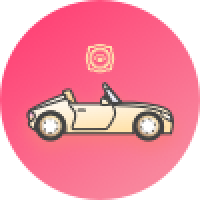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