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血”这个字无比清晰地钻入郎闫东的耳朵里,让他的心重重一抖。
转身,他跳下T台。
昏黄的光线下,只见纤弱苍白的女人倒在了洁白的瓷砖地面上,地上一滩猩红的血,红湿了她素白的裙子和瓷砖。
是谁浑身轻轻颤着,迈不开一步。墨黑如玉的眸里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慌痛?
要扶靳茜的那个女人被那血吓着了,一个趔趄摔坐在了地上。
周边人声嘈杂起来,可是没人敢轻易上前碰一下靳茜欢。
靳茜也感觉到了下身崩了一般有潮湿的东西涌出来,她手往身下一揩,满手的血红,把她自个儿吓得颤抖,怎么会有这么多血?
这绝对不是来了姨妈,经痛也这不会这么痛这么多。
有一种不祥的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,眼泪抑不住地滑下来……
“东子,你还站在那边干什么?帮忙啊!”奶奶也意识到靳茜的不寻常,老太太喜欢靳茜,当然不希望她出事,她的声音都嘶哑了,“茜茜,别怕,奶奶在呢……”
郎闫东猛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,身子又是剧烈一震,慌乱了步伐,几乎是跌撞着跑过去,颤抖着抱住她微微发凉冒汗的神态,看着她惨白脸庞上的泪痕,唇轻轻磕碰着,却发不出一个字。
怎么会这样?
第一次他骇怕这样触目惊心的鲜红,第一次他骇怕会失去一些什么,第一次慌乱到不知所措的地步,太多个第一次……
“靳茜,你别吓我。”
最后,他震颤着声带,对着痛得拧紧眉目的她,粗噶地从喉头挤出这几个字。
渐渐的,男人那一双永远处变不惊的眸里氤氲起淡淡的雾气。
“痛,我好痛……”靳茜恍恍惚惚地闷哼着。
“还愣着做什么?快送去医院啊。怕是孩子保不住了。”
奶奶厉声催促道,狠狠一劝擂在了郎闫东的胸膛口,可郎闫东竟不觉痛,因为比起心房的痛,奶奶那一拳微乎其微。
男人哽痛了喉,嘶哑地一遍遍念着,“靳茜,坚持住,坚持住,千万别有事,千万别……”
湛蓝听到有人在议论靳茜好像出了事,提着长长的裙摆,只身折了回来,看到的却是郎闫东抱着虚弱不堪的靳茜冲向门口,她看向靳茜的腰臀下都是血,涌出来似得,把郎闫东的手染红。
郎闫东脸色铁灰一般,苍白的唇线抿紧着,匆匆看了她一眼,就向外跑去。
她的心像是漏了一拍,不会的,茜茜不会出那种事的,那么好的一个姑娘……
要不是为了自己,靳茜也许就不会出事。
湛蓝湿润了眼眶,踢了脚上高跟鞋,紧紧跟着跑出去。
楼下救护车早就来了,却是掠过他们,朝隔壁索菲特酒店驶去了。
门口有从索菲特匆忙跑过来的大批人群,个个脸色慌张,像是受了巨大惊吓似得,有人问那边出了什么状况。
来人气喘吁吁说:“哎……那边刚发生枪击案,新郎官和新娘子好像都中了好几枪……”
“不会吧。枪击案?那人呢,死了没?”
“中了那么多枪,身体就是破了几个洞似得飙血,能活着才怪?哎……吓死我了,还好逃出来了。”
“什么深沉大恨啊,要在人结婚的时候把他们夫妻全杀了?”
“谁知道呢?我就是一服务员,端菜走到门口,就看到那群人丧心病狂似得拿着机枪对着那对新人扫射,就像警匪片里的变态杀手。”
湛蓝猛地身形一滞,她知道的,今天索菲特大酒店是靳明瑧的婚宴场所。
新郎官死了?
湛蓝的脊背冒出冷汗,她拧身过去,问刚才说话的女人,“谁死了?新郎官是不是姓靳。”
“是啊,就是刚上过电视领了诺贝尔医学奖的那个名医。”
不等她说完,湛蓝拨开拥挤的人群,不顾一切地赤脚往隔壁那家酒店冲去。
那个女人在身后喊,“那边千万别过去,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被抓住?别人都要逃出来,你这是去送死啊?”
靳茜说,只要她开口一句话,靳明瑧就会回来她身边。
可她从没想过,靳明瑧会出事?怎么能出事呢,那人已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出来,怎么能这么轻易出事呢?
眼泪迎着逆风不断刮落,脚底已经被路上石子划破,每走一步都留下一记血脚印,她不相信他会出事,他那么聪明的人,不是号称最强大脑吗?
这样一个睿智的男人,怎么可能死于乱枪扫射之下?
她不信,一步步艰难地跑过去,看见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抬着好几架担架从酒店门口出来,她想,会不会是靳明瑧?
她咬牙过去看,一个个看过去,都不是,最后那一个担架上的人被整张白布兜着,后头跟着眉头紧锁的江烨,她一下子绝望地泪崩,心中的
tang信念亦崩塌。
靳明瑧真的……死了?
江烨一抬头也看到了她,猛地一顿步,吃惊地张了张嘴巴,“秦小姐?”
湛蓝扑身过去,双腿一软,扑到了那架担架上,埋头趴在那白布下的尸体上埋头痛哭。
医护人员有点蒙,“你是死者家属吗?”
湛蓝哭得太悲切,肩膀一耸一耸的,一抽一抽的,说话也说不连贯,“是……我是他……老婆……”
江烨纳闷地拧了拧眉头,抬着担架的医护人员说,“那走吧,跟我们上车吧。”
湛蓝点了点头,发软的双腿颤巍巍地站起来,正欲跟他们离开,却听得身后传来男人熟悉的声音——“秦湛蓝,你何时改嫁给死人了?我怎么不知道?”
湛蓝心眼猛地一跳,不敢相信地缓缓拧过身去,从模糊的泪眼里,看到了暖光映射下仪表堂堂的男人,他微微挑着眉,诧异地看着她。
他没死?那白布下的是谁?她明明听到人们说,这里发生了枪战,新郎和新娘都一命呜呼了……
湛蓝用手背用力擦了擦眼睛,江烨叹了口气,小声提醒了一句,“这里面躺着的是司仪。”
湛蓝睁了睁眼,悲喜交加地望着这两个男人,泪光中噙着一点仇视,这江烨也真是的,干嘛不早说,害她白白掉了这么多眼泪?
江烨垂了垂眼,又小声嘀咕,“我本来想说的,可是被——”后面的话没再说下去,小心翼翼地用眼神指了指身旁的那个罪魁祸首。
这个节骨眼上,靳明瑧还戏弄她?
湛蓝一恼,扭头便走,可脚掌受伤不轻,刚刚来得急,一时忘了,现下可真是疼得要命,她脚瘸了一下,靳明瑧看到在水泥地上落下的血痕,眉心一敛,上去一个弯腰就将女人给抱起。
“来这里,不就是来找我的吗?还穿着婚纱,这想嫁给我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。我今个儿心情好,便从了你。走,我给你处理下脚上伤口就带你去领证。”
再见到这个男人,周身萦绕着男人的气息,她是激动的、幸福的,亦是安逸的,可猛地想起靳茜,她听得关于靳明瑧出事的消息一时将靳茜的事情抛到了脑后,现在想来,真觉对不住靳茜。
“茜茜出事了。我们先去医院吧。”
——
直到医院,郎闫东不知一路上闯了多少红灯。
“医生呢?妇科医生在哪里?”他一冲进医院大门,就疯了般地大喊大叫。
“这里是医院,不是菜市场,请你被乱吼,要找妇科医生,上三楼。”一个护士出来阻止咆哮的郎闫东。
大夫瞪了一眼气喘吁吁跑进来的郎闫东,又看向他怀里的女人,皱眉斥问,怎么大出血了?
“快,请你救救我老婆。”
鬼使神差的,他就把这个女人称呼成了自己的老婆。
那是他第一次用低声下气的口吻对一个人说话。
大夫点点头,让护士推车把病人推进手术室,说要立即动手术。
——
等在手术室外的郎闫东,从未觉得几十分钟可以比一个世纪过得还慢。
他站在手术室门口,半依着冰冷的墙,从烟盒里缓缓地掏出一根烟,点上火,两指夹着,指头轻轻颤着,慢慢送进嘴里,深深吸了一口,重重吐出。
她怀孕了?他从未想过她会怀孕,他跟她之间从未做个避孕措施,怀上孩子也不稀奇吧?可是那孩子又会不会不是他的?
可是不管是不是,他都不希望她出事,不明究竟,他就是莫名的恐慌,他这样腥风血雨里趟过来的居然也会恐惧如斯?
突然间,他意识到,他竟不怕自己会死,却怕她会死。
没过多久,靳明瑧和湛蓝来了。
湛蓝脚底板受伤不宜走动,靳明瑧给她置备了一张轮椅,让她暂时坐在上面,他推着轮椅走过来,愤愤睇了郎闫东一眼,“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,我要你偿命!”
郎闫东不吭声,懊悔地低着头,死劲地吸着烟。
“明臻,这是意外,他也不想的,要说责任,这事你我就没有了?”
是的,靳茜出事,他们都有责任,靳明瑧告诉她,是他让靳茜来阻止她和郎闫东的婚礼的,不管是报纸一事,还是跟许晴假结婚,都是他一手安排的,为的就是引出眼镜蛇,再将之除掉。
只是,这样的代价里不该包括靳茜,靳茜是最无辜的。
靳明瑧紧了紧双手,脸色铁青。
——
手术室的那盏红灯一暗,他微微一喜,也突然意识到手上传来的疼痛,手一抖,手指上的那一段烟灰落下来,竟是被烟灰烫了,自己竟浑噩不知。
他手一弹,丢掉烟头,走过去问出来的医生,靳明瑧推着湛蓝也跟着上前,听得郎闫东声音紧张担忧,“她怎么样了?”
“做人老公的怎么这么不当
心?她怀孕一个多月了,不过好在她意志力强,那孩子也是个生命力顽强的小家伙。孩子算是保住了,以后好好养着吧,她身体情况不太乐观,别再出什么差错了,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。”
郎闫东听到她跟孩子平安无事,嘴角不觉微微扬了扬,好在,她安好。
向医生道了谢,跟着被推着出来的靳茜一起进了病房。
湛蓝却阻止了要进去的靳明瑧,“给他们一些空间吧,茜茜没事我就安心了,等明天我们再带着汤圆一起来看她。”
——
术后,靳茜醒过来,一睁开眼便看见郎闫东。
郎闫东也看着她,却轻轻笑着,眼下一抹青黑。
靳茜不说话,只是静静看着他,眼里无一点波澜,就像在平淡无奇地看一个陌生人。
郎闫东有些害怕看到那样连一点感情都不带的眼神,即便是一点恨意也没有,他别开脸,默自问道,“要喝水吗?我给你倒。”
说着,便给她倒了半杯水,递到她唇边,她干裂的唇动了动,却没去喝,手轻轻一抬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将水泼了他一袖。
他眉梢紧了紧,想要爆发,却隐忍住,淡笑说,“你不喝水,是饿了吗?我让人去给你弄点吃的过来,要吃什么?”
他不知道为何自己要这般忍气吞声,其实他并没有错不是么?他还没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究竟谁的?
她仍盯着他,不吭一声,眸光却冷得可怕慑人。
他终究无法再容忍她这样恶劣的态度,沉声说,“靳茜,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”
她则看着他,淡淡的笑了,眉眼弯弯,恍若晨风,语气却薄凉,“那便请郎爷走罢。”
他拳头一捏,没听错,她叫他郎爷,带着距离的陌生的称呼。
“谁准你这么称呼我?”郎闫东暴戾地吼道。
靳茜看着愤怒的他,只是微微一笑,好似在看与她无关的一个小丑。
郎闫东很讨厌那种感觉,想挑起她的一点怒意,却偏偏被她完全忽视掉,他真想把她所有的淡定都捏碎掉。
他握着拳,走过去,一把捏住她的下巴,恶狠狠警告,“靳茜,别用这种态度对我,我很厌恶。”
她却仍像个无事的人,只看着他幽幽的笑,那是一种任你做什么,都无关痛痒的姿态。
他两眼气得要瞪出,胸腹也随之起起沉沉,看着她那张干干的唇,恼恨交加地一口吻住她,紧紧含住她一双唇,用自己的唾液在她唇瓣上润了润,许久才松开她。
“孩子,谁的?”
终于,他按捺不住,忍不住开口问道。
她一只手轻轻揉了揉肚子,勾唇浅笑,望着他,眸光坚定,语气淡淡道,“如果我说是你的,你信么?”
郎闫东一怔,看着她眸子里的淡静凄美的光芒,心想,真的会是他的么?
她看到他那一丝犹疑,他这是不信呢。
她阖了阖眼,用垂下的眼帘掩住眸里淡淡的伤感,再缓缓睁开,凉凉地牵起一边唇角,轻轻道,“不信,不是么?既然不信,又何必问呢?”
“小狼,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我们就到此为止罢,我再也不纠缠你了,我累了,你走罢。”
郎闫东听到“最后一次”四字时,心不觉猛的一缩,僵硬地楞在那里,不知该何去何从?
她真的不再眷恋了,她说话时极平淡镇定,嘴角一直挂着一抹释然的笑意。
靳茜心性似乎变了,那个俏皮明媚的女子消失了,若非被他伤透了心,又怎会这样?
他一直以为自己最想要的女人是湛蓝,可当看到她浑身是血的那一刻,他坚定的心彻底动摇,似乎他最在意的女人是靳茜,也只有靳茜。
“你叫我走,我就走,我岂不是很没面子?”
突然的,他很想用力搂住她,狠狠的堵住她的嘴,不让她说出那些他讨厌的字眼,也让她能正视他。---题外话---全文完,番外什么的不打算写了。后面的故事留白给大家任意YY吧。感谢大家一路支持。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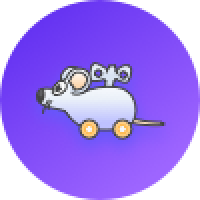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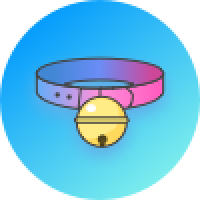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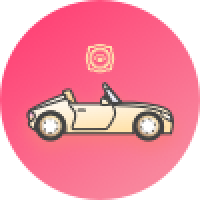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